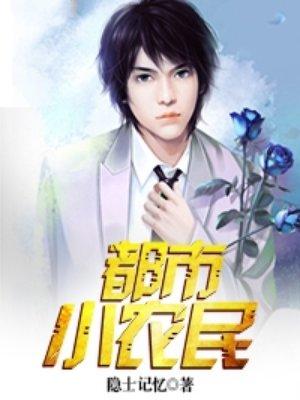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艳客劫 怎么样 > 第54页(第1页)
第54页(第1页)
曲南一苦笑一声,抬手便弹了绿腰一个脑嘣。绿腰风中凌乱了。她需要用尽全力攥紧手中的香炉,才不会将其砸到曲南一那张笑吟吟的脸上!她竟被一个男人弹了脑嘣?操-蛋!太-操-蛋-了!:又有女婴被偷曲南一刚出了水云渡,李大壮便迎了上去,压低声音禀告道:“大人,又有一女婴被偷走了。”曲南一翻身上马:“走,去看看!”李大壮翻身上马,紧随其后。二人来到老何家,见那大着肚子的妇人正在院中独自垂泪。妇人的男人叫何有银,此刻已经去粮店上工了。院子里长了些杂草,屋子也破损得厉害。看得出,这家人能在县里讨生活,依仗着的便是老何在粮店打工的微薄收入。那妇人见县太爷亲临,慌忙间站起身,踢倒了脚边的小马扎,噗通一声跪倒在地,身子瑟瑟发抖,说不出一句话来。曲南一让那妇人起来回话。妇人战战兢兢地站起身,却因为腿软,几次险些跌倒。曲南一一边在院内走动,一边询问道:“你且说说,你那娃儿多大,是如何丢的?”妇人磕磕巴巴,前言不搭后语,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李大壮看着着急,便插话道:“大人,这妇人胆小如鼠,怕是讲不明白。不如属下去把她家男人叫回来,大人一问便知。”妇人突然抬起头,惊慌道:“不不……不,大人,不能叫夫君回来。民妇……民妇能说得明白。”曲南一十分认真地四下巡视一圈,从角落里拎出一条缺了腿的小马扎,吹去浮灰,袍子一掀,坐在了上面,道:“讲吧。”妇人目瞪口呆地望着坐在小马扎上仰视着自己的县太爷,膝盖一软,又要跪下去。曲南一阻止道:“你也坐下,慢慢和本官说。本官最是亲民,不会轻易发怒,你且宽心,慢慢说。”妇人犹豫再三,终是扶起了小马扎,撅着屁股,小心翼翼地坐在了马札边上。曲南一又问一遍:“你的娃儿多大了?如何被偷的?”妇人未语泪先流:“民妇家的娃儿两岁了。民妇也不知道她是如何被偷的。民妇只是像寻常一样,哄睡了娃儿,自己也睡了。醒来后,却发现娃儿不见了。”曲南一问:“你夫君呢?”妇人老实地回道:“夫君去泰合粮店上工了。”曲南一问:“为何不叫他回来?”妇人瑟缩了一下肩膀,仿佛十分惧怕她的夫君。她怯生生地回道:“夫……夫君,夫君知道会打死民妇的。”看来,这何有银还是个爱孩子的好男人。曲南一问:“你夫君昨晚不在家?不知道娃儿丢了?”妇人回吸了吸鼻子,回道:“在,在的。”拿眼偷偷扫了曲南一一眼,小声道,“夫君知道娃儿丢了,可不上工就要饿肚子,民妇肚里这个可扛不住。夫君若是知道此事惊动了大人,非教训民妇不可。”曲南一发现自己误会了何有银会发怒的原因,于是追问道:“为何?”妇人又拿眼偷扫了曲南一一眼,带着试探,小心翼翼地回道:“民……民妇家里没有……没有银子,没有银子能孝敬大人。”呵……原来是因为银子才会对妇人动手。曲南一斜眼看了李大壮一眼。李大壮立刻涨红了脸,解释道:“没没,大人,我们没收她一个铜板。”曲南一摇头道:“孺子不可教也。本官是问你,她家既然不肯报给衙门知道,你又是怎么得知他家丢了一个女婴?”李大壮一怔,呆愣愣地回道:“属下听人说的。”曲南一挑眉:“听谁说的?”李大壮回忆道:“今儿一早,属下正往县衙里去,听见有人在属下耳边说了句,‘西头何有银家里也丢了一女婴。’属下转头去看,却不见人影,只有路上的几个行人在赶路。属下怕是有人故意戏耍属下,也没放在心上,本不欲查,可一想到那人说的是‘也丢了一女婴’后,记起四天前曾有人报案,说家里丢了一个女婴,这才打了个激灵,跑来查看一二。“起初啊,这妇人啥也不肯说,后来被属下一吓,才说了实话。也只说娃丢了,不敢惊动官府。”百姓们普遍认为“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你别进来”,倒也可以解释那妇人为何不想报给衙门知道此事。她怕女婴找不回来,还得搭上孝敬银子。家里本就拮据,若被其夫君何有银知晓她不安生,准没好果子吃。曲南一点点头,示意李大壮接着说。李大壮接着道:“属下看这事儿有些古怪,便回县衙去,想禀告给大人。大人不在县衙,属下就四处去找。打听了好久才知道,原来大人去看张天师的关门大弟子去了。属下不敢耽搁,就跑去求见大人了。”曲南一站起身,他屁股底下的缺腿小马扎便咣当一声倒在了地上,吓得那妇人又是一阵哆嗦。曲南一拍了拍身上的灰,对那妇人说:“莫惊慌,走,带本官去那娃儿住的地方看看。”妇人、女婴,还有何有银,都住在一张由木板搭建的简易床上。那屋里有扇窗,却小得可怜,一个女人想要从那里钻进去的可能性不大,如果是个男人的话,那就更无可能。屋里的门,晚上是插上栓的,并没有被撬开的痕迹。贼人偷窃物件不会挑家里有人的时候下手,但若是偷女婴就不一定了。尤其是两岁的女婴,必然在娘的照看下,不会任其一个人在家。只不过,谁会偷女婴呢?且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她带走,还不能让她发出一丁点儿的声音。思及此,曲南一问那妇人:“昨晚,你睡得可沉?”妇人回道:“民妇肚里有个闹腾的,睡得并不沉。”曲南一问:“没闻到异味?没听到任何声音?”妇人寻思片刻,回道:“民妇只听到了夫君的鼾声,闻到了……闻到了夫君的脚臭味,和……和屁味。”曲南一微微一愣,险些笑出声。他想到这妇人刚刚丢了娃儿,自己这笑来得有些不太合适,于是他生生地将笑意忍了回去,憋得脸都皱成了一团,甚是辛苦。妇人见曲南一皱眉,误以为夫君的臭味残留在屋子里没散干净,于是挥动衣袖,试图让屋里的味道闻起来不那么难闻。曲南一呆不下去了,勉强在寒酸的小屋里转了一圈后,喊上李大壮一同回到县衙。:曲南一与白子戚的奸情吃过饭后,太阳也快落山了,曲南一懒洋洋地躺在榻上,像一只渴睡的大花猫。这时,另一名衙役由外进入内堂,与李大壮这般那般耳语一番。李大壮便对四仰八叉躺着的曲南一说:“大人,白子戚来送银子了。”曲南一的眼睛一亮,点头,示意让他进来。虽说白子戚送银子不够痛快,但胜在持续不断。曲南一对今晚的青菜炒青菜极其不满意,这不,马上就有改善伙食的机会,他自然欢喜。白子戚走进来的时候,曲南一已经端坐而起,且十分亲切地唤了声:“白茂才。”白子戚敛衽一礼,道:“曲大人不必客气,唤我子戚便可。”曲南一笑眯了眼睛,像一只得道成仙的老狐狸精。他说:“本官素来公私分明,待白茂才将罚银和赔银悉数上缴,你我二人才好论交情不是?”白子戚绷着一张清秀的脸,点头称是。曲南一发现,白子戚此人比花青染还无趣,若是那绿腰在,呵呵……这些无趣之人反而会变得十分有趣。想到绿腰,曲南一忍不住唇角上扬,心情愉悦。这时,李大壮上前两步,回禀道:“大人,那何有银已被带到。”曲南一既不想动地方,也没见白子戚有走的意思,便让李大壮搬了一块屏风,挡在了二人面前,用以隔绝何有银的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