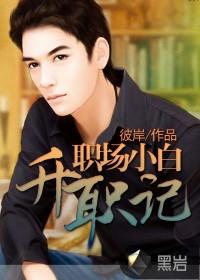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师尊在上萌徒在下免费阅读 > 第2页(第1页)
第2页(第1页)
宵随意却显出不解之色:“我不是小仙。”老鸨更是唯唯诺诺,“明白明白。仙人下凡自是不能言明身份的,老婆子我嘴严得很,绝不会说出去。不知小仙有何安排?”宵随意不知如何解释,想到昔日这婆娘对自己百般凌虐,如今这般低声下气,也算是因果报应,遂也不解释了,便当自己是个下凡的小仙吧。他正色道:“百花宴上,有个叫柳权贞的男子会来此处,不管他点什么,你皆不要理,将我带给他便可。”忖了忖又补充道:“此人前世曾有恩于我,我此次下凡,正是为了报恩。此事关乎天界机密,只可你知我知,不可向他人透露,否则后果如何,你应该清楚。”老鸨深信不疑,连连点头。宵随意挥挥手:“好了,我乏了,你且下去吧。”老鸨随即矮身退出门去。————所谓百花宴,不过是芳仪苑中自恃姿容与才情的倌人展露自我的无聊宴会罢了。这三个月内,宵随意倚仗着仙人身份,吃香喝辣,好不惬意。更是将那老鸨使唤得团团转。老鸨乐此不疲,觉得能服侍小仙,乃是三生有幸。终到百花宴至,老鸨推开房门,笑盈盈地告诉宵随意:“您的人来了。”此时外头明月初升,苑内早已张灯结彩,人流如潮。苑中正厅有个临时搭建的高台,已有女子在上面翩翩起舞,周遭鼓掌叫好声此起彼伏。更有人一掷千金选中一花,只为一夜春宵。又见衣衫不整的倌人扶着嫖客盈盈而过,或闻杯盘狼藉声与娇喘声于厢房中连绵交织。皆是纸醉金迷之景。老鸨领着宵随意在其间穿梭,走得腰板笔直,步履稳重,一丝风骚不敢卖弄,浑似从了良。二人很快来到二楼一处倚栏雅座。雅座左右两面以屏风相隔,正前方对着一楼高台,靠走廊一侧垂以水晶珠帘。其间隐约可见青衣男子自酌自饮的慵懒身影。宵随意的心脏忽然提起来,期盼之人就在眼前,他却慌乱多于喜悦。老鸨做了个请的手势,便识趣地走开了。冰凉的珠帘略过宵随意的脸颊,他缓缓步入站定,却只呆呆盯着地面,不敢抬眼瞧上一瞧。脑中不由映现出前世与柳权贞的相遇之景。哪似如今这般顺理成章。那时的自己,因不接受被姨娘卖入勾栏院的事实,始终不肯就范,屡次妄图逃脱,毒打与挨饿乃是家常便饭。便是在这腐烂的百花宴上,他熬着一身伤,躲过老鸨的耳目,缩瑟在柳权贞的脚下,哀求他——“救救我吧。”那人道:“行啊,先给我磕个头。”一个头又何妨。宵随意未有半点犹豫,何止一个头,他咚咚咚地,直至磕到额头流血才罢休。这些记忆深处的陈年旧事,以后便只有自己一人知晓了。“我分明点了这苑里头牌,怎么来了个乳臭未干的小屁孩儿?”不满声响起,打断了宵随意的心绪。柳权贞宵随意仓惶应道:“柳公子有所不知,今日苑中举办了百花宴,排的上名号的佳丽都要在正厅中的高台上献艳献艺,花魁亦不例外。若要点,需待那花魁演绎完毕,您出重金赛过其余来客,方可得那一夜春宵。”手指哒哒敲着桌面,柳权贞不着边际道:“你说话时为何不看我,我不好看吗?”宵随意有些无措,“自然不是,柳公子好看得很。我只是……只是有些害羞。”哪里是什么害羞,不过是近故人,情更怯罢了。“你都未看我一眼,怎知我好看?”剑鞘末梢忽地抵住宵随意下颚,轻轻挑起,迫使他抬起头来面对眼前之人。四目相对。执剑之人凤目上挑,带着些微戏谑睥睨之色,道:“长得还不赖,这趟花酒不算白喝。”随即收剑,略一摆手,“过来给我斟酒。”宵随意仍是怔怔立在原处,忽觉鼻子发酸,两行浊泪竟顺颊而下。柳权贞莫名其妙,“这好端端的,你哭甚?”宵随意抹去眼泪,换作笑颜,只道:“没什么,见公子生得比那花魁还美,内心难掩激动。”如此吹捧,令柳权贞颇为受用,直夸他是慧眼识珠之人。宵随意一瞬不瞬盯着他。这才是柳权贞该有的模样,傲气、自恋,爱喝花酒,潇洒恣意,而不是将情感拘泥于一个女人,一个带他踏入深渊的女人。斟了半晌酒,柳权贞喝喝停停,间或对搔首弄姿的花倌评头论足一番,不是赞美,而是挑刺。一会儿嫌弃妆容太过浓烈,一会儿鄙夷舞姿不够柔美,既说身段逊色,又言歌喉粗糙……总之,没有瞧得上眼的。“倒是你,清秀些,看着让人惬意舒适。”宵随意知其是随口一说,却也暗暗高兴了几分。柳权贞又道:“看了这许久,这些所谓的美人真是千篇一律的难看,腻了腻了,好生无趣。喝完这壶酒我便走了。”听他说要走,宵随意自知不可再耽搁,即刻弃了酒壶跪伏于地,埋首道:“公子,走之前,可否带我一同离开?”柳权贞本是等着空杯斟满,却换来这一出。挑挑眉,索性将那杯盏丢于一边,睨着他道:“这是何意?莫不是要我给你赎身?”宵随意道:“我知您是得道高人,带一个小娃娃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不过是易如反掌的事情。”“啊……那就是要我带你私奔了?”宵随意觉得用词不妥,急忙纠正,“不,并非私奔。只是我厌恶这烟花之地,想要脱离苦海。”“哦……那我凭什么要帮你?或者说,我帮了你,你要如何报答?”“当牛做马,甘之如饴。”柳权贞嗤笑:“愿为我当牛做马之人多如繁星,你有甚特别?”宵随意知他会如此问,脱口道:“坊间听闻玉琼山有位真人,常着青衣,道法超绝。又爱研习边缘秘术,却苦于无人试术,他这爱好便只能自娱自乐,上不得大雅之堂。此乃他生平憾事,不得消解。”“你说这些作甚?”“柳公子,我愿做那试术之人,使您求仁得仁,无所嗔怨。”一席话毕,室内静得出奇,四面欢愉之音显得尤为喧嚣。良久,柳权贞终是忍俊不禁,“有趣有趣,原是有备而来,倒叫我始料未及。”转眼却是敛起笑意,伸脚勾起宵随意脸来,面上意兴阑珊,眼中尽是厌倦之色。“那坊间可曾传,我门下本有不少试术者,如你这般,初生牛犊,一派虔诚。然未过多久便惧怕不已,擅自逃遁了。”宵随意辩道:“世人多狡诈,我却不同。”“哪里不同?”他随即咬破手指,小心翼翼捧过柳权贞一只手,道了声得罪了,便以血代墨,在其掌心圈圈绕绕,作出一片符阵。那符阵闪了一抹微弱红光,便消失不见了。柳权贞反复观摩,觉得颇为稀奇。“我自认见识过人,却是头次见到这种阵法,是做什么用的?”俨然不关心阵法对自己是否会有伤害。宵随意看着他道:“此术名唤如影随形,以血为媒。术成,则握阵者对画阵者有绝对控制权。只要有命令之词,画阵者便能不顾一切去完成,至死不休。”柳权贞双眼发光,此物甚投其好。“若真如此,我当场试试如何?”“您尽管开口便是。”“那好。你便从此处跳下去,以证你之诚。”前尘(一)高台上葳蕤之色被无端坠落的孩子打破。霎时尖叫声四起,人流如惊禽。却见一青衣男子携剑飞身而下,如轻燕般将那即将坠地的孩子凭空托起,牢牢搂于怀中,衣袍翻飞,乘风越空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