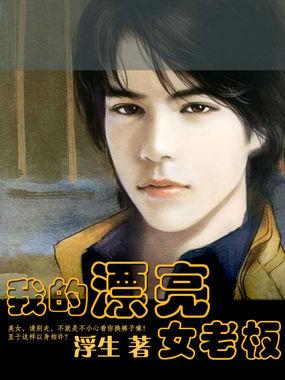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及时雨作文400字 > 第48页(第1页)
第48页(第1页)
然而他摇摇晃晃地下了两级台阶,遥遥望见九曲十八弯的园区小径间,跑来一个?焦急的身影。自从进入景观设计这一行,巩桐出入工地频繁,平时还会有意去逛园子、锻炼身体,跑步速度比高中时快了不少。但她与生俱来的体能太?一般,一百米左右的弯曲距离仍旧能跑到气?喘吁吁。巩桐停在江奕白跟前,一面喘着粗气?,一面打量苍白无力的他,脱口?而出:“你没事吧?”江奕白双眸盘旋惹人惊骇的红血丝,意识逐渐粘黏混沌,怔怔地看?着她面含忧虑,跑到凌乱的鬓间碎发。后面有经?理敏锐地感觉到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大着胆子接话:“江总病了,该去医院,但他不愿意去啊。”“我们怎么劝都没用。”“那不行。”巩桐不假思索,瞧见江奕白浑浑噩噩,状态可以说?是?跌去了海沟,下一秒就会一头栽去地上,长躺不起的样子。她急火攻心,伸手就去抓他的袖子,逼迫不听话的小孩似的:“走?,必须去。”指尖触及昂贵西服面料的刹那,巩桐骤然打了一个?激灵。她十分怀疑江奕白得的是?病毒性流感,还是?传染性最强的那一种?,她已?经?惨遭传染,把容量有限的大脑烧成?了碳灰。她居然完全忽略了眼前人的身份,江奕白可不是?她下面那些可以随意安排,乖乖听令的组员。巩桐正想放手,抓紧时间补救一声“抱歉”,一动不动盯了她半晌的江奕白却迈开了脚步,缓慢跟上了她。巩桐愣住,指腹不自觉在他的衣衫上摩挲了一下。附近那些经?理也?看?得目瞪口?呆,左右传递眼神。巩桐更加感觉掌心贴合的布料的滚烫,手指徐徐松懈,试图放开。奈何江奕白皱起了眉峰犀利的剑眉,暂停了脚步,用一双早已?被强势病魔折磨得模糊的眼睛瞅着她,似是?传达不满,无声催促。巩桐心下一跳,不敢再松手,一路将他送上了车。她清楚他身边缺什么也?不会缺人,打算就此离开,那些紧随其后的经?理却劝:“小姐,您没什么要紧事情的话,和我们江总一起去吧。”“江总似乎会听你的劝。”江奕白靠去汽车的后背,痛苦难耐地闭上眼眸,却似本能地反手一握,抓住了她运动外套的袖子。巩桐惶恐,使劲儿想要抽出来,奈何发现无能为力,面料被他越拽越紧,整只袖子都快遭了殃。她及时拉住险些垮下肩膀的外套,无可奈何地盯他几秒,短叹一声。着实令人意想不到,有人平常西装革履,冠冕堂皇,一生病就退化成?了小孩子。巩桐完全拿一个?病人没办法,默念两声“好人做到底”,又一次坐上了江奕白的顶奢宾利。几位经?理有胆子做说?客,却不敢贸然把自家大老板全部?交给一个?普通合作方,几辆汽车有速地追在后面。抵达距离最近的三甲医院,江奕白脸色又白了几分,上了几重?可怖乌紫的双唇紧紧压成?一条线,强忍着一般。他的体力明显下滑得更严重?,脚下虚浮,全靠一位人高马大的经?理搀扶。但他的另一只手却相当执着,牢固地团住巩桐的衣袖。巩桐垂眸看?看?他落在自己浅灰衣料上的葱白手指,甚至想过既然他这么喜欢抓这件衣服袖子,干脆脱下来给他。然而念头一转,不到十月的季节还未迎来强降温,哪怕巩桐再怕冷,里面也?只穿了一件配套的运动内衣,万万不敢在公共场合随便松散外套。她只得由着他,小步跟在他身侧。在急诊科走?过一圈,测出江奕白高烧到了三十九点八度,医生结合他近期混乱的作息,安排了输液。他应该也?相当困倦,躺去病床没多久,输着输着液就合上眼,沉沉地睡了过去。那几个?经?理相互看?看?,不约而同地退出了病房。巩桐坐在床边,听见江奕白的呼吸声渐渐归为平缓,耐心地等了许久,确定?他果真是?睡着了,再次尝试去掰他的手指。睡熟状态下的江奕白再也?没有那股孩童式的执拗,手指变得尤其软,巩桐轻轻一使劲儿,便拿开了他的手,毫不费力。外套总算是?得以解放,连带着她这个?人也?能够摆脱束缚,彻底脱离这间病房,远离眼前的男人。然而巩桐起身给他盖好被子,见他在睡梦中无意识拧起的眉头,仿佛万分痛苦一般,她又没来由地回到了原位。急诊科素来是?一家医院最为混乱莫测,嘈杂的科室之一,外面人满为患,喧嚣难止,反衬得几平米的病房内部?异常安静。巩桐默不作声地坐在陪护椅上,详细打量江奕白现如?今的睡颜。突地,她耳畔炸响了他很久以前说?过的一句话。十六岁的少年懒洋洋趴在赵柯的座位上,扑闪惺忪的睡眼,拖着懒倦嗓音对她说?:“下次随便打扰。”那是?巩桐第一次幸之又幸,和他做过短暂的同桌,细致看?过他熟睡的模样。当时她听见这句话只觉得讶异,自知机会难得,不敢奢求真的会有下次。如?何能想到,她当真会再一次受到眷顾,拥有近距离地,无所顾忌地待在他身侧,看?他沉入梦乡的机会。哪怕回首一望,已?是?十年之久。而今的江奕白和高中逃离班队活动,跑来十三班闭目小憩的时期相差太?多,那时的少年纵情而为,无所忧虑,梦乡肯定?安然无恙,俊朗的眉目完全舒展,缠不上一丝一毫的烦愁。不似现在,他的眉心越锁越紧,如?同有千万愁绪围追堵截,纵然是?躲避现实逃进睡梦,也?无法得到庇佑,获得自由喘息。江奕白的睡相也?不再老实,除去输液那只手,其余四肢不时就在挪动,甚至大力踢了一次被子,一双又直又细的小腿露出来大半。他不过是?在医院输液几个?小时,用不着换病号服,身上还是?自己的西服裤。不知怎的,他不经?意的动作卷起了垂顺的裤腿,显露一截冷白皮肤。巩桐重?新给江奕白拉盖被子时,随意一瞟,注意到他左侧小腿蜿蜒一道刺目的旧疤。约莫七八厘米,缝合留下的痕迹隐约可见,扭曲狰狞。巩桐下意识抬起眼,去找他左手小拇指。重?逢的第一天,她便在江锦关注过他那里的伤痕。巩桐莫名感觉这两处疤痕的颜色接近,大胆猜测是?不是?同一个?时间产生的。就在她走?神思索的时候,揣在裤兜的手机忽然响了。响铃突兀而刺激,巩桐瞧见病床上的男人眉心轻动,手忙脚乱地掐断了电话。她给他盖完被子,退去通讯记录,查到是?赵柯打来的。对方的微信即刻追来:【在忙?不方便接电话?】巩桐坐回去,瞥了眼江奕白,见他不像是?马上要苏醒的状态,放心地打字:【嗯。】赵大胖:【忙什么呢?在哪儿忙?马上就是?晚饭时间了,你不要又不吃饭。】巩桐如?实回:【医院。】她指尖不停,还没敲完下一句话,赵柯又发来:【啥?你病了?哪家医院?】【你不会是?胃痛到去挂水了吧?】巩桐:【不是?,是?一个?……】她余光瞟着病床上的男人,停顿半秒,缓缓打出:【一个?朋友。】虽然她也?不清楚自己和江奕白算不算朋友。赵柯没说?信不信,一个?劲儿追问:【哪家医院?我看?有没有熟人。】巩桐知道他这些年凭借一张巧嘴,在医疗系统混得如?鱼得水,积累了一部?分人脉,为了以防他源源不断地问,如?实报了医院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