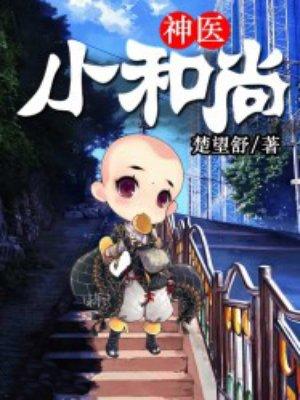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软玉在怀by花槐最新章节更新 > 第33章 妈妈(第1页)
第33章 妈妈(第1页)
唐辛原本没想喊石玉,怕上京这里认识他的人多,再一想那是他的事和她有什么关系,总好过突然间喊石墨的名字把孩子吓到。
喊完了心里有点虚,这算不算是扬名立万?连她都要在上京城里展露头角了?
那就露吧,她这趟来就是要把石玉拿下的,还怕人知道?
她就怕没人知道。
据梁桥说,惦记石玉的女人不少,只是敢下手的几乎没有。
唐辛不以为意,能有多难?
一回生,二回熟,就这么简单。
照着石玉的意思,三回她都熟能生巧了,足见压根就不难。
所以唐辛底气十足,石玉两个字喊得声势更足,整个园子里霎时间安静下来。
什么声音都没了,落针可闻。
坐在二楼的男人也听见了,动作微滞,随手将蟹放回碟中,慢条斯理地拿起手巾擦了慢步踱到围栏边,朝
唐辛正踩在一张四方桌上,刚好对上视线。
头发上沾的雪化成了水,脸被风吹得有些红,眼角也是红的,瞪向他时如嗔如怨,就像昨日午后他见到的那张脸。
只是外面的雨换成了雪。
情状也像,他在上轻松俯视,她在下极力仰望。
唐辛一看见他眼尾带起的笑就也想到了,脸绷得更紧,再一看,父子俩搂抱着的样子霎时与梦中画面重叠,同样气人。
拉开了架式却不好当着孩子的面发作,唐辛愣是迅速地挤了张笑脸,又被石玉似笑非笑地盯了一会,莫名的脸上有些烧。
也像昨日。
分明不乐意,还要装出副欢喜状,不知道她还能忍多久。
石玉连笑都不忍了,一下下轻拍着石墨的背,唤她:“上来。”
唐辛怔了半刻,从桌子上跳下去,随着重新开锣的鼓点走上楼去,越想越不对,怎么跟叫猫似的,他叫,她就巴巴地上去了?
怎么不是他下来呢?
鼓点渐快,促得她脚步也快,来不及不满转眼便到了二楼的包厢。
一层转角台阶跑得腿软,气喘吁吁。
人还没站定,便听见一声“妈妈”,满溢着情感和相见的喜悦。
唐辛心理瞬间舒服多了,应了一声定睛看去,石玉已然坐回到椅子上,腿上坐着石墨,不远处还站着个小男孩。
两双黑白分明的眼睛都在盯着她看,一个开心一个好奇,只有石玉垂着眼眉,不疾不徐地剥着蟹壳问她:“怎么这样就跑出来了?”
唐辛不知道自己哪样了,听见他又问:“冷不冷?”
声轻,说得缓慢,特耳熟,昨天才和她这样说过一回。
唐辛特别怕冷,一场雨就看出来了,缩在被窝里面一点缝都不许露,热得他一身汗,幸好她身上凉丝丝的,抱着倒也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