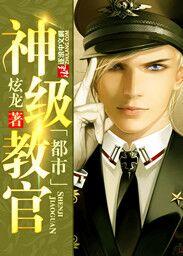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误踏春在线 > 第22页(第1页)
第22页(第1页)
此后他每日卸了兵甲,头一件事便是奔去西边营帐探看万红庵的景况,滞留在其间的时辰,倒比待自己营帐内还多些。如此两头奔忙,自然分身乏术,顾不得许多细要。其间有晓霭的信笺传来,又是嘘寒问暖关怀他身体,又是嘤嘤咛咛地细诉情浓,他粗略扫过几眼,还未及回信,便不知佚落到哪旮旯里去了。
斗转星移间半月过去,万红庵逐渐睁眼,初时还只能扳着他的嘴滴进些汤药,其后神识回转,身上伤疤也已显露结痂愈合的迹象,便每日可喂些清粥淡汤。
这日孟柯人才卸甲归来,昌晏就附身在马前叨咕了几句,但见他眉头一皱,下马径自往西边营帐里走了。
一入帐,见万红庵塌眉耷眼地半卧在铺席上,神情恹恹,十分憔悴消沉。帐中气味也不很怡人,除药汤的焦苦之外,还掺杂着些难言的腥臭。孟柯人面露恚色,倒不是因着气味,而是见不得万红庵这副消怠模样:“怎的,听昌晏讲你使嗔犯娇的又不肯进食?人还没死,倒巴巴撵着去作活尸。”
这话讲得冲人,万红庵也不搭理,轻轻拢了腰上的薄被,侧过身去,拿背向他。
瞧着万红庵这般作态,又思及自己近日衣不解带地操劳奔波,孟柯人心下大为不忿。见杌凳上还剩着半碗残粥,便端过去,扳过万红庵一边肩膀,就要来灌他。
万红庵自然忸怩不肯,纵不顾气虚体弱,也强要挣弄几下。两人过招几回,万红庵是一通软绵绵的乱攮胡推,而孟柯人到底顾忌他病体,不好下重手,哪里是个搏打的架势,倒好似一对猢狲互挠。
不一时铺席被二人搅得稀乱,万红庵面皮涨红,倒真有几分情急模样。孟柯人也不肯泄气,拿手肘掣着万红庵,硬是将粥碗抵到他嘴边,填进去几口。再要强灌,万红庵便不肯了,挥手将粥碗打落,黏黏糊糊洒了满铺。
“你这犟驴托生的,今朝着实欠打!若还乔张致,便兀自乔去,只看这一身细嫩皮肉,捱不捱得过我三拳。”孟柯人看着一片狼藉,也失了耐性,只当万红庵刁蛮冥顽,故意在那间拿乔作态,这便喝斥几声,又抬手要去掀他被褥。
那被面脏污,本当是揭去的与下人洗晒的。不想孟柯人甫一探手过去,万红庵脸上便颜色顿失,紧捂着身上薄被,无论如何不肯与人。这落到孟柯人眼中,自然又是与他作对的派头,当下色勃神厉,遽然伸过手去。
盈盈一层薄被揭起,先迎面扑来一股烂臭,只见那被遮掩起来的铺席上,赫然呈着滩湿黄秽物。秽物上头还有团滑腻嫣红的物件,不是别的,正是那截本已被塞回万红庵体内的肠肉。孟柯人一时愣住了,手僵在那间不知是收是放,脸上恚色全消,竟露出几分窘然无措。
万红庵早已面如死灰,双目空洞,两瓣薄唇颤颤地抽搐几下,忽然以手掩面,哭出声来。
那日他肠肉被严玉郎捣出,虽是被医官塞回,可自能吃些许粥食后,便时时觉得下头松松脱脱,似有什么东西将要滑出。晌午昌晏得了孟柯人授意,要督着他多用些饭食,可那清粥才下肚半碗,他便觉出腹中异样,不肯再用下去了。果然才遣退昌晏,窍门便兜揽不住,一股秽物淅沥沥排出,而随着秽物带出的,还有软乎乎湿腻腻的一截肉。
万红庵早啼过一场,从未有而今这般厌弃自己的躯壳,恨不能剐了一身去,落个干干净净、轻轻巧巧。横竖也没什么活头,身子被折辱成这副模样,本就使他苦痛难捱,再一想旁人会对他如何奚落讥笑,更有如利匕一刀一刀捅进心窝。
他心知孟柯人向来鄙夷轻贱他,所以左掩右藏,无论如何不肯在孟柯人面前落了丑。堪堪天意愚弄,这般脏污狼狈模样,到底还是落进了孟柯人眼里。
第四十一章
想往昔弁华园中,万红庵何等殊丽照人,谁人不仰慕他的姿仪,垂涎他风情?一张姣颜难描难画,莺见惭,燕见妒;细腰婑媠,玉肌生香,恣意一摆胜过几度春光;玉足娇翘,十指纤纤,信来一拈更是人间风流。就把他比那仙子出离广寒,落榻凡尘,也是有人信的。
再看而今,满身是累淤积秽、腥恶熏人,臭皮囊只凭半口气吊着尚在,莫要提那仙子,便把他看作个活人,也颇有几分勉强。
这一时万红庵脑子里昏聩涨热,眼前乌泱泱一片,仿佛挤满了小人,个个嘲他笑他,拿了泥脚来践辱他。他惶惶怵怵,耳边又蓦地响起严玉郎那通恶言恶语——“现下便是把你扔到那姓孟的跟前,他也未必肯佝个腰瞅你一眼!”,心中大恸,忽然就双齿迸紧咬住舌头,想要自绝了性命。
孟柯人先还杵着,见万红庵是动了真格,才仿佛回魂一般,忙不迭地扑上前去,拿手掐他两靥,又去扳住下颌。待把两排银牙起开,那口里已是血淋淋一片,孟柯人怕他还不甘休,便把自己的手给塞了进去,供他咬着。
“我又不曾多数落你甚么,哪里就要这般作气!即便话说重了,往日`你也是个牙尖嘴利的,就不会还口吗?”孟柯人只当万红庵是被自己一席话激的,慌手慌脚间还不忘嘟囔几句。可人哪理会得他一通念白,早昏死过去。
再醒转,万红庵已置身一桶温吞吞的香汤当中,口里发麻发苦,是被清理后敷了药粉。
孟柯人半拉身子挂在桶边,袖管挽起,正拧着张帕子替他揩洗身上脏污,眉目低低垂着,眼角处竟有些湿红。万红庵轻轻动了动食指,被孟柯人察觉,再抬起头来,已换作副气势汹汹的模样,逮住他腕子兴师问罪:“你作甚么要自寻短见?”
万红庵自鼻底嗤了声,把头撇向一边,半晌才轻言细语:“死了好,活着生受嗟磨,死了倒干净利索。”
孟柯人听得气不打一处,想自己近日来奔波劳累、夜不阖目,做牛做马一般,身上衣衫都汗臭泛馊了。他天潢贵胄般的人物,哪里对人这般着紧过?却偏偏有人不识他抬举:“未必一条命在你眼里,就这般轻贱?”
见孟柯人发急追问,万红庵倒是一派从容,落落大方回道:“是,我命天生就是轻贱,合该不生在这世上。”他嘴角微翘,仿佛还带几分笑意,“我若不生在这世上,父母便不会枉死,祖产也不至于破败,我不识得甚的王爵公卿、达官显贵,不识得这颠三倒四、荒唐世道,也不受你们作践!”说着转脸又将嘴角撇下,声带哽咽,“殿下心底若还有些慈悲,便放我去了……这人间歪七扭八、藏污纳秽,没个落脚处。”
孟柯人听得浑不是个滋味,仿佛脸上连捱了数十个巴掌,肚子又吃了几拳,直要把肝胆呕出。见着万红庵又有几分情绪上头,似要发癔抽癫的模样,慌忙扑过身去把一双臂儿锁紧,将人箍在怀里。他仍旧防着万红庵咬舌,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将手往人口里塞去,被咬烂了也毫无知觉。
一阵闹腾过后,桶里的水儿被渐得四起,孟柯人衣衫也沁湿一片,浑身似个落汤拔毛鸡,好不狼狈。万红庵耗空了气力,便消停下来,由着孟柯人将自己从水里捞出,摆到铺上。
那铺席不知何时早换了新的,帐中味道清净许多,孟柯人将万红庵放下,在跟前一阵踅来走去,蹉跎好久才终于掀帘出了帐子。万红庵只当他是走了。谁知不一时,孟柯人复又折回来,往铺边一坐,就要去扳万红庵的膝头,把腿往两边拉开。
万红庵万没料到他会这般,当下慌了神,一阵推推搡搡。怎奈膂力不济,还不只得由人摆弄。却见孟柯人将他两腿拨开,小心翼翼地探手过去,轻轻将那挂在外间的肠肉揉进肚里,一面揉着还一面端察他神色,怕将他揉痛。
这情景着实羞臊煞人,万红庵此时头脑也清醒些许,觉着孟柯人那暖暖的指头正抵着他的肉,一点一点往里顶去,便情不自禁扣住了他的手,却推也不是,留也不是,亦不知该谢还是该恼。忸怩来去,便只好暗咬了下唇,默不作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