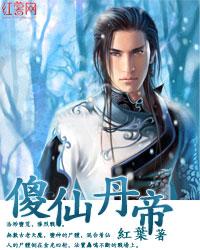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天津女记者豆瓣 > 第174章 雅室长谈(第1页)
第174章 雅室长谈(第1页)
如此这般思量来思量去,时间就耗过去好几分钟。唐书白本待要说的话,到了嘴边只得咽回去,换了一套新说法:“叫人出来又不说话,究竟什么意思呢?”
厉凤竹恍了恍神,牵牵嘴角,斟字酌句地慢慢说去:“东洋、英国都是外来势力,我都反对。但是换个角度讲,目前国人对于振兴中华无非是三种选择,靠欧美、靠东洋、靠自己。你选择了靠东洋,而我选择了靠自己。甭管怎么样吧,明人不说暗话。至少我们都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这点没有问题吧?”
她虽然是使出了满脑袋的力量,想要找到一个合理的逻辑,把谈话往合作方向去促成。可是,越是向下说,她倒越是露怯地不敢放出声音来了。她依然在想刚才的问题,无论是私情还是大义,她对于唐书白总是表现出立场坚定的一面,那么唐书白何必犯了贱似地非缠住她不可呢?
然而,唐书白对于这种丢失底气的表现,却根本不看在眼里,反是一本正经地答了话:“对,我从未抛弃过一个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感,我只是选择了我认为对的阵营。”
按照这样的话锋,只需微微一点头,那么两个人的合作就等于成功了一大半。
然而事情太容易了,厉凤竹这两日来总是为了这“容易”二字大感困惑。被绑走的儿子很容易就回来了,对于她在工作上的尴尬境地,也就有人帮着宣传她的难言之隐,使她很容易就获得了原谅与同情。包括约翰逊拆穿了她文字游戏之后,也是轻易就放过了她。尤其是唐书白,一反他平日的形象,总是很容易糊弄。
厉凤竹捡起手边的筷子,忙夹了两口菜送到嘴里,低着头慢慢地去咀嚼。人的思维仿佛总是这样滞后的。在迈出第一步的时候,觉得一层一层的道理都想得万无一失。然而真等到了紧要关头,脑子里又会忽然闪出无数个念头,告诉着自己当初若能前前后后多掂量掂量就好了。她现在就在发愁,要是听了徐新启的话,想在一切行动之前,或许会更稳当呢。
在唐书白的角度看去,厉凤竹的一双黑眸被额前的短刘海挡得几乎看不着,只在几绺头发的缝隙里,将将能窥见她的上下眼皮不住地开合。她又是那样斯文地吃饭,半天也不曾说出一个字。因之,唐书白反被她的泰然逼得有些发急了,试探道:“你打什么坏主意呢?一直都不说话。不会是想跟我合作扳倒约翰逊……然后,再跟约翰逊联手扳倒我吧。”
闻言,厉凤竹歘地抬起了头,她看见唐书白的脸色变得很难看,望过来的眼神中透着很深的失落。她又不由地去想,唐书白为何会对自己抱有如此违背常理的执着呢?因想着,身子就跟着一点点抬高,嘴里衔着淡淡的尴尬的笑意。一双筷子伸向菜盘子里拨弄了两下。挑菜这种举止是很失仪的,在一定程度上,她的这种小动作正泄露着内心之中从未有过的混乱和紧张。
“我一个孤女子哪有这么大的能耐。”厉凤竹缓缓地把嘴角高高牵起,“实告诉你吧,之前我选择了后者,但是约翰逊过于喜怒无常、过河拆桥了。我现在只想实行前一种办法。因为在讨厌约翰逊这一层,我们是可以达成共识的。”
在说话和吃菜的时候,厉凤竹的状态实在不大好,好几回不自觉地斜向上抬着下巴颏,把内心的犹疑暴露得彻彻底底。抬眼去看唐书白,在他的眼神中察觉不到一丝一毫的狡猾和阴狠,反而给人一种坦荡荡的感受。更有一份强大的包容力,无论厉凤竹多么地露怯,他都能够无条件地容忍下去。
只见唐书白浅笑着问道:“扳倒约翰逊,对你有好处吗?”
频频走神的厉凤竹没有立刻作答,眨巴着眼睛困惑地望了唐书白片刻,方才做发狠状:“他是我一个隐患。这个人实在太记仇,想要修补与他的裂痕,简直是痴人说梦。所以,我希望他离开津门,甚至希望他就此离开中国。”
“隐患……”唐书白冷笑着咂摸她的话,“你究竟是妇人之仁,只是希望他离开而不是消失。”
这里,厉凤竹重重地搁下筷子,叹了一口气,眼中一半是愤然一半又是退忍之意:“论私心,像他这样心狠手辣、满手血腥之人,的确该死。若有哪个肯伸张正义的人动手,我倒也肯鼓掌叫好。可你要我主动去举枪,我就办不到了。我心里很矛盾,自己是不敢也不愿逾越法律底线的。但这九国租界实在乱透了,种族早已凌驾于法律之上,有时想想以暴制暴是逼不得已必须为之的。然而我却……”
“别假仁假义假清高了。”唐书白说时鼻子里轻蔑地哼了一声,又道,“不会脏你的手,只要你动动嘴,自然有人愿效车马之劳。你若过不去心里那关,过后只当完全不知情,于你一点妨碍也不会有的。”
若从话音听去,这人的态度是狠辣而冷漠的,可他的脸上却始终含着和煦的颜色,给人言不由衷的错觉。厉凤竹更是不免想到了,他要果真如他所言那般无情,但对于我未免也太愿意帮助了。这又算什么意思呢?他很禁不住美色诱惑吗?未必吧,一个日日都不敢怠慢,愿意花时间慢慢去数稿纸的人,有这样强大的毅力,恐怕是国色天香也难令他神魂颠倒吧。
一连串的问题没还想透,却听门外有人一路笑着高声寒暄进屋,道:“难得唐主编大驾光临呀。”
来者声音柔中带刚,不见其人时,厉凤竹的直觉便猜是位白面书生。她随着唐书白一道起身相迎,手放在大腿上悄悄地掐了一把,借以振作精神。她今天有些不在状态,奇奇怪怪的新念头又太多了。方才想的种种问题不能说是无足轻重的,但此来为的是见一见东兴楼神秘的金经理,别的事再重要也必须先搁在一边了。
只见走进来一位穿长衣的英俊青年,衣着尽管很是传统,可是那脸上洋溢的神采,尤其是一丝不乱的分发,却给人一种说不上来的摩登感。
唐书白上前一路握着手,把人让到了座位上,笑道:“不敢当不敢当,金经理这样忙,还特地来应酬我。”
说话间,就有店伙进来添了一副碗筷。
厉凤竹站在原地只管微笑,那人看看她,复又瞧了瞧唐书白,眼中充满了好奇,似乎期待着唐书白以什么样的措辞,来介绍这位陌生的妇人。
唐书白的表示很是模糊,只介绍厉凤竹是一位厉姓朋友。这个举动正合了厉凤竹低调处理记者身份的小心思,不免大松一口气。转而在介绍那位青年时,完全是不吝赞美之词,既夸了他出身大家,又吹捧着他年少有成,事业经营得如何如何好。下了诸多褒义的评语之后,方才提到这人的身份是东兴楼的经理,姓金名碧辉,恰是金碧辉煌少一字,更是玩笑地表示由名姓上便注定了金经理是要荣华一生的。
这金碧辉仿佛与唐书白经常会面的,彼此间兄弟相称,坐下来你一言我一语地互相吹捧个不休。他有意多瞧了厉凤竹两眼,笑道:“密斯厉,你大概是初次来吧,我瞧着你很是眼生呢。我这所饭庄在菜色上是很齐全的,厨子的手艺倒也不赖,但也不能够说津门卫只此一家别无分号。不过,大家还是很愿意捧小弟的场,这里边自然是有一点缘故的。据你这初来之人的眼睛看来,我这里有哪一样是别的地方没有的呢?”
厉凤竹觉得金碧辉虽是初相识,却能表现得亲近而自然,确实是生来要做大生意的人。而这样的侃侃而谈,似乎弦外有音,因此她答起话来是谨慎而惜字的:“外中内西,结合起来别有一番风味,难以替代呀。”
话虽不长,倒引出了金碧辉十分玩味的样子,他对着厉凤竹微微颔首,眼珠子一转又对了唐书白呵呵地笑着。
再看唐书白,脸上同样是带着笑意的,与金碧辉照了照眼之后,低下头去兀自想着些什么。嘴角依然是上扬的,隐隐约约间却给人一种无奈之感。
倒是金碧辉兴致很好,不知为的什么,忽然拍着桌子大笑着说起来:“是了是了,果然的。我这‘果然’二字是很有意思的,听我慢慢对你说吧。当初我打算盖这所饭庄的时候,待在自家的书房中,整整画了三个月的图纸,把我从小在京时所见过的那一种繁华富贵景象都融在了纸上。更不提所找的那些匠人,你知道吗,非老手艺人我是不肯用的。可是呢,在如此传统的外观之下,我并没有选择表里如一的做法,而是引入了西洋的美学。在我这里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不养陪客的姑娘,力求做个新式的文明饭庄。”
看小说,630book。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