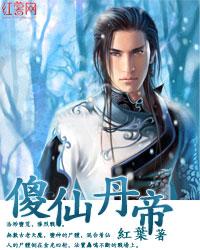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天津女记者豆瓣 > 第116章 逐渐孤立(第1页)
第116章 逐渐孤立(第1页)
蒋忆瑶背上一软,脑袋微微地点着,心道厉凤竹莫不是想越过徐新启直接向王富春致歉吧。这算计倒也符合她的行事风格,能不拖累人就尽量不去拖累。可是,她这种打算是算错了王富春的。这位主编大人近来是愈发对人而不对事了,这个歉恐怕道了也是白道。因想着,蒋忆瑶嘴里嘶嘶地对着厉凤竹吹了两口气。为引起她的注意,又冲着她把手不停地摆着。
王富春看在眼里,冷哼一声,人却还是朝前站的,丝毫不把厉凤竹的话放在心上。只见他抬了抬手腕,敷衍道:“我马上要见一位重要的访客,你迟一两个钟头再进来吧。”
蒋忆瑶虽仍坐在位子上,上身却拼命地掂起来,越过许多张桌子,和徐新启做着眼神交涉。其结果是,他也同样猜不透厉凤竹预备让事情向何处去发展。
至于厉凤竹,她低眸时恰巧发现王富春公文包里露着红封壳的一条长边,很像证书一类的东西。因为高过了拉链的位置,因此公文包只能敞开着。
糟了,他要会的贵客,难说就是传说中那位外聘的副主编呀。
厉凤竹不能坐以待毙,只得当着满社人的面,直接地开门见山:“主编,明天早晨会有一篇关于西南局势的评论文章发布。”
王富春在一片骚动声中,难掩兴奋地转头问道:“什么内容?”
这种神情提示了厉凤竹,王富春对徐新启的忌惮已经超越了压制,他甚至有意把徐新启踢出报社。正是因他过于强烈地执着于私心,才会轻易便被唐书白蒙蔽了心智。
“西南方面派出的代表……”厉凤竹上前一步,把声音放大了来说,“已经与山东、山西、陕西、四川、云南及贵州等省取得了联系,以期尽快协商出一致的立场。”
王富春满心欢喜由丹田提起来的一股气,因这句话彻底由热烈转至冰凉,刺激得他连连咳嗽了几下。
“你的消息,从哪儿来的?”当王富春勉强能问出话来时,脸色早已铁青了,还泛出一种红涨的怒色,染在一处像极了一颗发紫的茄子。
厉凤竹偷摸着吁了一口气,方才答道:“是我从前的同事,他给我看了已经送去排字的定稿。《津门时报》那边争取到了西南方面的许可,派去前线采访的是一名外籍记者,其立场相对来说是客观的,他的报道自然是切实可信了。”
王富春提包的手攥得愈发紧了,指节都是发白的。鼓了腮帮子,又是一阵猛烈地咳嗽。他强撑着哼了一声,道:“见报就见报,算什么了不起的大事,非要耽搁我的时间。又不是你拿到了许可,又不是你去了前线,又不是你写的文章!”
他的三个“不是”,吼得一个比一个响亮。恶意不止写在了脸上,同样也由那指指点点的姿态上彻底地表露出来。他是不好直接指责厉凤竹耽误了他安插副主编的计划,只好拿耽误时间来做一个挡箭牌。
事情棘手了,王富春虽然拥有津馆大小事务的决定权,但重要的举措依然需要向迁移至海州的本部进行汇报。沪馆那边对他外聘副主编的想法,没有给出肯定的答复。但听了不利于徐新启的那些传言之后,也没有很坚决地反对外聘一事。
王富春早就通过别的路子打听过了,所以他其实一早就知道了,徐新启这次恐怕是被谣言误伤的。但他不想放过这个可以借题发挥的良机,便打起了赶在真消息坐实前,先斩后奏把徐新启晋升的后路给断了的主意。甚至于就在刚才,他还异想天开地期盼着,万一厉凤竹带来的消息是,徐新启确实有隐瞒不发的行为呢。
屋里的气氛急转直下,像极了泥人铺,大伙儿都不做事了,也不敢说话。唯有一双双的眼睛,你望了我我望了你,许许多多的意思就在这沉默之中,流转了起来。
厉凤竹微点一点头,轻声笑道:“我的意思是,有些谣言也该尽早平息了。自月初时,西南局势产生了动荡,业内就一直在流传咱们报社有人拿到了独家内幕,却迟迟不肯拿出来发布,似是要依仗着这条独家来筹谋一个前途。若没有这些闲言碎语,我也不必巴巴地非要找您谈话。可我眼看着大家因一句流言,搞得一下猜忌这个,一下又猜忌那个的。同社的人非但不友爱,反而互相疑心起来,实在很不值当。我又是个急性子,因此连一个晚上都等不了了,非得这会儿就说清楚不可。”
王富春拿腔拿调地讥讽她道:“你倒是很有团体精神啊。”复扫视了一周,怒问,“真的有这样的谣言吗?这里的人,都有谁在参与呢?”
厉凤竹也跟着看向众同事,大家都是互相丢过一个眼神,便开始摇头否认。她最后把目光落在了,全程没怎么抬头的徐新启身上。
像是感受到了什么独特的气流一般,徐新启便也抬眸与之对视。他早就表示过,自己无意参与副主编的争夺,因此并不放出多少感激的眼神来。更深一层地想,社内气氛已然有些剑拔弩张了,此时接任实则是接个烫手山芋过来。
王富春对着大家冷笑一下:“不要怕得罪人。《大公报》是权威报刊,不是什么坊间小报,我们聘的都是专业人才,不是长舌泼妇。倘若有谁拿着良心记者的薪金,行的却是市井小人那套伎俩,我是坚决不欢迎的!如有人知道内情就赶紧说出来,算是替报社肃清门户做出一点贡献。若有人因私交而包庇维护奸人,那就是对报社赤裸裸的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