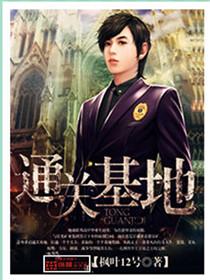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美人成欢花花卷子25章 > 第102章(第1页)
第102章(第1页)
楚曜容身上的伤只要不轻易挪动,伤口不再撕裂开来,成欢便放心。因此,听到林公公说只在嵩阳殿内不外出走动,成欢没有再去多劝。
都敢拼着命回都,又哪里能阻止他议事。他是普通人,可也是君王。
然而成欢并不知道的是,回都后楚曜容身上的毒又发了。
身上的鞭伤还在慢慢结痂,伤口呈现一条条红色的疤痕,新鲜的肉重新生长时还在疼痒,然而蔓毒一发,一种钻入心尖的疼痛覆盖了身上的伤痛。
楚曜容完全移动不了,从下马车时起,每朝宫内走的一步都似针扎。
就这样坚持到了晚上,安越请来了余师,才在嵩阳殿会诊。
嵩阳殿内门窗紧闭着,殿外廊边挂着金灿灿的灯笼,有一等守卫守在殿外,而殿内亮着灯光,隐隐约约透着一丝紧张严肃的氛围。
原先的护卫军全都由沈誉做了安排,楚曜容从少郢回都也是由那些护卫军护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楚曜容的出行都被护卫军监管。
宫殿由护卫军看守,殿内则是内侍宫人,直到楚曜容找机会提拔了林公公。
如今,护卫军在沈氏起兵后全部焕然一新,魏蒙从魏家军营里精心挑选了几队将士任职护卫王宫,如今站在殿外的都是真正的护国护主的将士。
余师看了一眼紧闭的门窗,皱着眉头看着榻上脸色苍白的男人,放下手中的药帕,问道,“怎么还将门窗闭那么紧,外面如今不都是您的人?”
都是他的人,还怕个什么。
楚曜容右手紧按着自己的心脏处,乌青的唇干巴巴的,但他额上还在不停地冒汗,听到余师的话,他勉强笑了笑,说道,“这屋药味重,还是不便散出去让人闻着了。”
“能散到哪去?”余师拿药帕往楚曜容嘴里塞,楚曜容汗流的太多,因此唇都干的出血,余师便拿浸了秘药的帕子给他解解。
楚曜容咬住帕子,人略带腼腆地朝余师笑笑,示意他不要打开。
一向说一不二,手段威严的君王居然这般表现,余师一下子便明白了个大概,他看窗外几眼,笑着道,“怕她闻着?那你这掩掩藏藏也瞒不了多久,还不如让她看见,多多心疼几次。”
余师这话半是玩笑半是认真,楚曜容却摇了摇头。
他若能痊愈,便还好办,让她心疼一下自己,还能意外收获她的心意,可这病,偏偏容易要了他的命。
刚想完,楚曜容咳嗽起来,吐出药帕,帕子落在被子上,接着他又吐出了一口带着黑色的血水。
吐黑血还是第一次,楚曜容看着被子上的血渍,眼里的色彩又黯淡了几分,目光深沉地看着金丝蝉翼被上绣缝的双飞喜鹊。
余师也惊讶地看着,没有顾虑地拿起那带着血渍的帕子,凑近打量了几番。
“这药还不曾是如此效果啊!”余师改良了几番药园里的药,听说沈裳吃了都能吃活,经他改良又怎么会让人吃吐了血。
楚曜容倒是没有怪罪,他看着那块血渍,低着头沉声道,“恐不是因那些药。”
不是因为药,而是因为他身上的毒。
蔓毒都渗入心脉了,吐出来的自然会是黑的。
余师看楚曜容一眼,低声叹了口气,说道,“王上也不用悲观,在下再去找找法子。”说完,他站起身来,吩咐宫人几句后,便离开了殿内。
药园的药方既然能医醒沈裳,那一定是有些用处的。想着,余师脚下步伐加快些,手里紧紧捏着衣裳的口袋处。在他的口袋里面,有两块方帕,一是刚被楚曜容吐了血水的帕子,另一片帕子里则包裹着点点稀碎粉粒。
等人离开,很快有宫人过来更换新的被褥,宫人刚上前拿走脏的被子,楚曜容便吩咐道,“不必拿去浣洗,直接烧了。”
说完,他扶着床头的柱子,慢慢地坐到榻上,唤走殿里的宫人后,自己一个人靠在床头边,看着外面的月色,思索。
他自幼时被送往少郢别宫,先王从未看过他一次,兄长也只偶尔过来几封书信。
之后,父兄陆续身亡遇难,他则被一封诏书召回大都,先王未来得及写上一封继位遗旨,却将沈氏禁锢大都的死令给了他。
所有的重压都在那一瞬间给了他。
如今沈氏已败,但他也落得个病弱之身,之后,又该如何使得大历兴耀?
曲陵给他留了封遗书,里面写了几个法子,但是,他如今又拿什么去做到?
极大的疲惫感向楚曜容袭来,眼皮渐渐变重,他垂下头,慢慢闭上眼睛。
不知过了多久,门外的林公公悄悄推开殿门,随后朝一旁低声道,“娘娘,您进。”
成欢独自走了进来,殿内灯火黯淡,几处烛火燃尽之后未再点亮,她看到珠帘后的人影,轻声唤了一句,“王上?”
里面没人应答,成欢撩开珠帘走进去,就看见斜靠在榻上的男子,穿着一身洁白的里衣,任由月色洒落在他的白衣之上,眼眸紧闭着,眉头耸高,微微皱着。
他看起来很累,成欢轻声走近,将落在地上的被子拿起,盖在他的身上,然而她刚弯腰靠近时,目光朝他身上看去,人一下子僵住。
在月色照不到的左胸之下,洁白的衣料上是有一大片似擦身而的红色血迹,淡淡的一层紧紧碍着男人的衣料,可血色泛的黑色又十分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