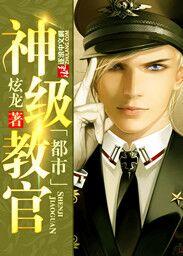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夜色撩人烛火摇曳 > 第二十九章(第1页)
第二十九章(第1页)
周黎,是周磊唯一的血亲,世上最亲的亲人。
周黎回来了,罗安失眠的毛病竟然莫名的好了。这里的因果道理实在是不足为外人道也,而且,就算罗安自己,心里也未必百分之百清楚。
还有半个月就过年了,周黎一边在网上找年货,一边抱怨:“你说我哥他们领导不是有病么?什么学习啊还连电话都不让打?昨天我给他们队里带电话,何哥说他也不知道。”
此时,俩人一人一台电脑,罗安的是台式机,周黎抱着笔记本坐在罗安的床上,稀里哗啦地刷团购。过年是个集结号,把全国人民都吹起来了,千人大团随处可见,那折扣打的,周黎就觉得不点鼠标手痒痒。
罗安在给自己的店上传新片图片,过年么,她当然不能落后。
“小黎,你看看这个包,哪个角度有感觉?”她让开身子,让周黎帮她选照片。
周黎伸着脖子端详半响,指着那款四十五度角侧面的照片说:“这个,看着就来派。”
罗安自己瞅了会儿,从善如流地把照片上传。就听周黎无比惆怅地嘟囔:“这个真是便宜的天怒人怨啊!哎,也不知道我哥啥时候从集中营出来。”
罗安眨眨眼,乐了:“你是不是没钱了?”
“唔……”周黎手里没钱真憋屈的慌:“安姐我跟你说,你可别告诉我哥啊,我这回回去参加婚礼,把这几年存的钱都随了。我三叔家也过得不咋好,小辉他媳妇,别的都不算,彩礼就要了四斤——你知道什么是四斤不?”
“项链、耳环、戒指……还有啥?”难道还有脚链?只听过三金,没听过是四金。
“呵!咱给你科普下啊——人民币,一沓新币上称正好四两,四斤是多少,你算去吧!”
“十万!”罗安惊着了。
“嗯,就这人家还老不乐意,说现在都是六斤八斤的。瞧不上我三叔家给盖的房子,说了,要把房子卖了去兴城买楼,毕竟以后孩子还得上学呢。这我三叔家都拉了饥荒借的,等他们真买楼的时候还有的闹呢。”
“不是给他们十万了么?让他们自己买去呗。”
“那是彩礼钱!我们兴城吧跟一般地方还不一样,给人家的彩礼钱就是人家的,要是娘家心疼姑娘,私下里给姑娘带过来也是人自己的私房钱,明白了没?再说,现在新婚姻法卡得死,婚前婚后、你的我的,分得明白着呢,这多好哇,先把彩礼要了,然后婚后买楼,啥时候都不吃亏。哎呀把我三叔难得!结婚头天三婶还打吊瓶呢,这哪是结婚呐,催命呢么!”周黎捧着心口,“哎我的攒的那两个香香钱呦~想起来我就心疼!”
罗安本来挺感慨的,后来就忍不住笑了起来:“不用心疼,你是随礼的,总能见着回头钱儿滴,等你结婚的时候你那香香钱儿的就回来了,说不定还能拖家带口弄点儿利息呢~”
“嗯?”周黎双手拇指,“安姐v5!”紧接着咣当倒床上,“可我没钱了啊没钱了啊没钱了啊~”
罗安乐不可支:“呐!你面前现有低息无抵押小额贷款业务,要申请不?”
“低息?你也好意思你?!”
“嗯哼~怎么地吧?爱贷不贷,有能耐你找你哥去!”
周黎捋胳膊挽袖子:“我还真就……真就找不着!哎,安姐你说,我哥不是犯事儿了吧?”
“犯……啥事?”想到那一沓沓钱,她心里咯噔一下子。
“比如生活作风问题,哈哈哈哈!”
“……”
周黎从罗安那里转了两千的血拼钱,就一脑袋扎到团购里不出来了。倒是罗安,难得在下午的时候出了门。
罗安觉得自己有病,还病得不轻。下午出门的第一件事儿是去律师行咨询了一下受贿的量刑问题。
前台给她介绍的律师是个中年胖子,一听罗安的问题就来劲儿了,眼睛里的光刷刷地,问题也一个接一个抛出来:“你说的六万是总数还是一次的数目?已经被对方掌握在案的具体数字是多少?是固定资产还是现金?你家人在哪个部门任职?交个朋友吧……”
罗安满头包地跑出来,律师还追着问呢:“小姐,你留个电话啊,这是我名片,以后常联系啊。”
罗安白扔了五十大元的咨询费,一个人站在大马路上想哭。
头两天的积雪正在融化,人行道的清雪力度不如主干道,还有好些个雪堆堆在行道树下。十字路口人来车往,乱乱糟糟。
“姑娘,买报纸吗?不买你换个地方站行不?大娘就靠着报摊养活自己呐,你站的可真是地方~”
罗安连说对不起,走出去几步又转回来,买了份儿报纸。
卖报纸的大娘很海派,大冬天脑袋脖子裹得严实,却不耐烦戴口罩,两颊冻得通红。看罗安特意照顾她生意,很大方地赠送了份儿昨天的报纸,按老太太说,卖了也是钱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