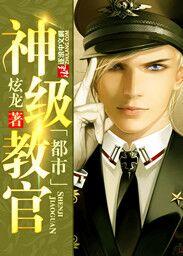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长公主重生后又美又飒 爱吃大白菜的兔子 > 第37章(第1页)
第37章(第1页)
二人在数日中互相装模作样,彼此都心知肚明。现下狄从贺忽然将一切摆上台面,容洛摩挲袖炉花纹的手指微微一顿。莞尔抬眼。
“如此本宫更不该相信于你。”不再惺惺作态的模样上带了点冷意。细长的两道眉舒开,宽和的面目,却似乎只是一张花灯时的观音面具。容洛松了松双腿,手中的袖炉轻轻晃一晃,“内闱敌对明确,宝林既不属于皇后,又不属于母亲与本宫——墙头枯草,本宫可是怕得紧。”
话语庄肃。狄从贺却好似听到了什么好笑的事物,嗤嗤一声掩面笑出来。眼中暗色盈盈,笑得自嘲又开怀。可莫名有一股沉沉的死气。
容洛凝望着她。见她抬袖沾去眼角泪珠,含着笑说道:“墙头与否是另话。只是这份名单殿下着实要信。原玉家并非向氏家臣。是戚悠有心讨好向氏女,这才费力做了玉家的义女,将玉家拉拢到向氏麾下,做了向氏助力。”她垂袖在旁。细软的双袖凌乱的滑过蒲席,“花名录中人虽不是向氏女手中所有臣子。但其上每一人都与向氏、玉家同有来往。此次玉家一事向氏摘得干净,妾身不愿相见——仅希图殿下将此名录交往谢家,逼陛下施压向氏。”
字字带着寒气。容洛静静听了片刻,招手让宫婢替自己束发。何姑姑侍奉左右,领命上前,临着扫了狄从贺一眼。眸中复杂。
狄从贺是皇后手中一柄极少出鞘的横刀。她光亮而锋利,每一次展示于人前,必定沾染上许多人的性命。这十余年她被皇后掌控,令人闻之畏怯。众人眼中她对皇后尤其忠诚。可现在她却在皇后敌对之女的眼前,请容洛借谢家之力,裁去向氏羽翼……
未免太过荒唐。
香炉紫烟袅袅升起。指尖微微抚过裙袂上细密的针脚。容洛敛目思索片刻,倾唇扬声:“宝林为皇后所用之事,本宫始终都知。想来你聪明如斯,合该同样。”木梳自发间一次次落下,簌簌的声音与容洛嗓音相叠,没有一丝情感,“亦是这般。本宫也未可知此事是否你与皇后的一计。毕竟皇后欲伤谢家之心路人皆知,本宫不可不疑心。”
重谢两家在朝中势力极大。其中谢家掌控文臣脉络,朝中文臣如非中立与皇帝一方大臣,定然依附谢家与下属世家,事事以谢家为先。皇帝势力虽经过五年发展,渐渐壮大,到底如何比不上谢家百年世家来得根基深厚,一分也动摇不了谢家,因而也忌惮谢贵妃。对谢贵妃在后宫所行之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全当不知。
这般行径自然要向凌竹无比眼红。她比谢贵妃入太子府晚了一年,入府后因父家权势不比谢贵妃,各处都矮谢贵妃一头,还被谢贵妃抢走了主母管家的权利。而入宫之后,谢贵妃又得谢家荣耀撑腰,直接受封贵妃。许多嫔姬看此纷纷对谢贵妃溜须拍马,令她一时失势,险些掌宫权利也要被夺去。尤实不能不将贵妃恨之入骨。
而此心在容洛前世时便亲眼得见。对皇后亦十分忌讳。
“殿下信或不信。妾身都不能做主。”静默许久。狄从贺仿佛也理解容洛的猜忌。缓缓一笑,她伸手撑着蒲席站起,乌青色的衣衫单薄软柔,两页披风抖落踝边。“妾身允诺向氏女假意投诚,为的只是将这一封名录交到殿下手中。其余的,妾身也做到那地步了。”
容洛扬眼。翛然似乎觉察到了什么,模糊质问:“你替她做了什么?”
狄从贺掩唇。风韵犹存的眉目间溢出一分真心笑意。虚睇容洛一息,她拢住披风,走进飘渺游离的漫天雪花之中。
。
明德宫中心绪不宁。狄从贺却是极其平静。
步出宫门。狄从贺将绒帽罩上头顶,在穿行的宫人中假作一个染了风寒的掌事宫女,脚步迅速地往受厘宫去。一时无异。直到她跨过第六道拱门时,扬眼撞上了在此地等候她许久的陈公公。
宦者约莫三十好几的年岁。方圆脸,眉毛稀疏,细长的双眼里仿佛坛着一汪冰冷的黑水。路过的宫奴无一人不对他福礼。
是慈仁宫里的近侍总管。
看见他。狄从贺格外镇静。
陈公公与狄从贺常有来往。彼此也熟稔,见着她的模样,知她清楚自己的行径已然暴露在皇后眼皮当中。也不再多说,手中拂尘一扫,半躬了腰,恭恭敬敬道了声“娘娘请宝林”。便与左右一齐将她带去了慈仁宫。
眼下卯时三刻。苍穹才燃了点旭光的颜色。慈仁宫中诸人开始洒扫,见她入殿,一声大气不曾出,静静收了手里的东西,一一退了出去。
向凌竹一向醒的极早。狄从贺站在堂下时,她正坐在上座,细细的品饮着一翁雪水烹出的顾渚紫笋。
敛了裙,狄从贺从善如流地在下方跪下,语调缓柔:“妾身给娘娘请安。”
光景一如这十数年来的每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