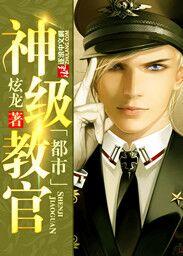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春满傣乡葫芦丝曲谱 > 第83页(第1页)
第83页(第1页)
桨已经摇不动了。它被石子夹击,几乎寸步难行。
众人下船来,不得不踩着梆硬的石子上岸。这有点虔诚的意味。
爹将我背在背上。娘牵着姐姐的手。我们是幸福的一家人。是金家人。
姐姐因脚步一滑,掉在矮矮低低的水里。那水里有几近腐烂的水草。姐姐坐了一屁股的褐绿色,顿时哇哇大哭,叫着“好脏!”娘被她这一嗓子嚎得胆战心惊,急忙捂住她的嘴,“不准哭!丢死人了!”
而我从爹瘦削的肩线,定定朝下看,果真看到鹅卵密布的河床上,在那涓涓细流中,有一丝一丝的玫红色。“是小鱼吗?”我问爹。爹低头细看,说不是。那是年轻姑娘脸颊落下的胭脂。于是我又回头看水中央的碧绿色,笃定道,“那边是水草吧。”爹说,是。“水爱它吗?”我问了个很古怪的问题。而爹面庞凄清,“疾风知草劲,水里的草,终归还是太柔软,太无用了。”娘突然插嘴道,“你也晓得!这次辞官,就是激流勇退了。劳烦你心头,务必要尘埃落定,从此后,我们就是寻常人,不要再做青云之梦的念想了。”爹颇为无奈地点点头。我捋一捋爹头上的白发,突然问了个更为古怪的问题,“爹,你和娘爱我和姐姐吗?”爹说爱。
再后来,有了陆大人那档事,爹不带我看大夫,执意让我挂着血淋淋的伤口去京城,作为告发陆家的罪状。于是我们一家人,也是经过同样的水路。在船上,我又问,爹,你爱我吗?爹突然战栗,沉默了许久,才说爹爱你,娘也爱你,姐姐也爱你。
您还有没有更爱的人?这是我一直以来的疑问。
但我永远不能问出口。
船行到中央便落寞地折返,我们最终没有去到京城。
水草生得太密了,我们没法去到对岸。
我也没到我人生的对岸。
再到后头,爹被陆家那一党人迫害,失足坠落身亡,娘带着我嫁进了罗府。罗府和陆家一直都是一条船上的蚂蚱。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娘对罗大人的信任,可见一斑。我进罗府时,才只有六岁,但我看到罗大人那谄媚卑微的神色,就知道他是个没多大出息的人。
我成了罗浮。
罗大人严令禁止我自称金小年。
这里是罗府,怎么会有姓金的人?
罗大人生气时,总吹胡子瞪眼。
我想他忘了,他早年随爹念书时,曾那样为金先生的才华所折服,殷殷切切地说,“金先生,要是我能和您再亲近些就好了,真想直接随您姓。”
也不知道罗大人和金先生早前的师徒关系,是不是罗大人至今仍旧只是个“通判”小官的原因。陆派的人,多少有些忌惮吧。他们都那样运筹帷幄,思维缜密。想到这里,我想,我还是要感激他的。谢谢他的保全,我和我娘,还能苟活于世间。
但我决不能原谅罗策和罗潜。
罗策比我大六岁,罗潜较我年长五岁。
我到罗府时,只有六岁。他们也正是调皮捣蛋的年纪。
姐姐性子比较烈,能哭能叫,他们不太招惹她,于是我成了唯一的靶子。他们两兄弟将我装进兜小猪的篓子里,把我来来回回地踢来踢去。我受不了大伤,只是会被偶尔冒出的竹片割伤手臂。
罗策甚至将我一人丢去过陆府,他分明知道陆大人有多恨金家,而我就是金小年,这是所有人心照不宣的事儿。我被罗策拐骗到陆府后,他也有过愧疚,常常在门边等我,捧着一些很精致的糕点或者女孩儿喜欢的玩具。我将所有的物件丢进下水沟里。我把我被拔下的带血的指甲拌进他的菜汤里。我也不喜欢那些布娃娃,用剪刀剪下过它裹脸的臭布。
只是这样的屈辱,像是一把利刃,它将我的心割裂成数十瓣,我永远只能在世上漂浮。且娘也告诉我,要忍耐,忍耐到徒手握住荆棘,我们在别人的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这是做人的本分。于是我从阳关灿烂下的鲜花,长成了沟壑里
但还是会在夜里想起很难堪的往事。这样,日久天长的,我果然成了怪物。我跟姐姐说,我的脑袋里好像有一窝刺猬,拱得我头疼,我好像和以前不一样了,姐姐你能原谅我吗?
姐姐有些惊讶,将我抱在怀里。
我们靠在一个枕头上。
我妹妹的好,就像是天上的月亮,姐姐我啊,一抬头,就能看到。你偶尔的错漏和小脾气,就像一根蒲公英上的细绒,我稍稍吐口气,就全都飞走啦。
姐姐永远对我温柔。
但我对这样温柔的姐姐,说了两个大谎。
第一个是在中元节时,家家铺子前都搁了一盛水的铜盆,顾客的铜板要丢进去,以验是真钱还是鬼钱。能沉的,就是真的。因为传说,中元节这一日,鬼门大开,街道上有百鬼夜行。我分明看到铜钱沉下去了,却指着水盆,斩钉截铁道,那铜钱浮在水面上。这将掌柜和姐姐都吓得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