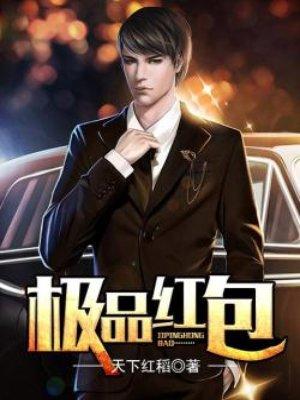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封神榜圣人 > 第九十七章 姜尚怒愤休马招娣(第1页)
第九十七章 姜尚怒愤休马招娣(第1页)
“你等既欲存生,便不许在此害民。”白鹤童子去时所留雷符,乃是保命之用,姜子牙如何舍得在用一张,这便挥手道,“你等这便去吧,寻一静地,若能潜心悔过,他日自可修成正果。”
“多谢仙长慈悲!”五妖性命得保,自是欣喜非常,急忙忙叩首,“仙长隆恩,我等粉身碎骨也是难报舍命之恩,愿从此归于仙长一侧,牵马执蹬,权作感恩孝敬。”
“这……”姜子牙新来朝歌,更无熟识之人,宋家之人,亦不好差使,见五鬼诚恳,亦可做差遣之人,这便同意下来,“如此也好,你等这便随我归于宋家,切记,莫要惊扰了他人。”
五鬼听命,这便隐身随行,马招娣在家中久候多时,迟迟不见姜子牙归来,心中自是着急:“这人不过卖些笊篱,如何这晚未归,莫不是拿了那钱,去朝歌鬼混?”
姜子牙新得跟班,自是要好好进行一下思想教育,这便将玉虚宫中,所学所知,尽数显摆出来,五妖乃是山野鬼魅,如何听过这等奇闻,自是认真非常,听得仔细,这一讲演,时间自然晚了,直到亥时,才踏着月色归来。
马招娣苦等姜子牙多时,见之自言自语,急急忙出来相迎:“相公此去多时,不知赚了多少银两?”
姜子牙忙得一拍膝盖,心中暗叫不好,前番妖凤忽起,便将笊篱吹得不知去了何处,后有得了五妖随同,自己大喜过望,已然将赚钱之事,丢在了脑后,这将面色一红。
马招娣见姜子牙不说话,面色骤然冷了下来:“未转银两,那笊篱去了何处?”
“回家路上,巧逢妖物劫道,此番只顾降妖,那笊篱已然不知去处。”马招娣一介凡妇,如何见过鬼神,只道姜子牙唬骗自己,这便大怒道:“你这贼人,莫不是将那银两花了,却来唬骗与我?你且说来,是不是在朝歌城中会了哪个相好!”
“马招娣你休得胡言,我姜尚怎会做那龌龊之事!”听姜子牙直呼自己名讳,马招娣顿得一惊,尔后便是大气,一手揪住他之衣衫,这便撕扯:“若不会相好,怎会一张铜板也未带回!”
“混账!我姜子牙岂是那种不肖之人!”
“那你倒是将今日所赚银两拿出啊!”
“今日未赚银两,我说之你如何不听!”
“未赚银两,如何到了深夜放回,你定是在朝歌有了旁人,才会如此!”
“混账!我虚活了古稀之年,从未见过你这等泼悍之人!”姜子牙正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这般欲哭无泪,更是心中郁闷,这是哪一辈子做下冤孽,如何欠了此人缘分!
马招娣听姜子牙咒骂,心中更是恼火,这便起身,与之拉扯起来,五妖亦没见过如此不讲理之人,可此乃主人家事,众人如何说话,这便早早撤去,以免祸及自身。
这边宋异人放欲入睡,听得旁屋吵闹,心怕出了祸患,急急跑来:“贤弟、弟妹,深夜不好好安睡,这是做甚?”
马招娣一见宋异人前来,更是哭得梨花带雨,急忙哭道:“宋伯伯不知,你这贤弟……你这贤弟,竟在朝歌有了旁人,将今日所赚银两皆花费在了那人身上!”
“今日赚的银两,什么银两?”宋异人自然不知今日之事,姜子牙受马招娣之扰,自不敢说鬼神之事,只得言笊篱被人抢夺了去,自己怕妻子责怪,这便回来晚了。
“姜子牙!你休要胡言,那笊篱能值几个银两,谁人会抢?你骗我不够,还在花言巧语,哄骗宋伯伯!”马招娣听闻此言,更是闹个没完,宋异人无奈之下,只能将姜子牙拉出:“贤弟啊,若得人选,在宋家成亲便是,如何惹出这等祸事?”
“这……咳!仁兄啊,那笊篱真是丢了,你我八拜之交,还不知我人品如何?”姜子牙更是有苦不得说,这便将马招娣叫之赚钱一事,俱与宋异人诉说。
“哈哈哈……原是如此,赚钱岂不易尔,贤弟明日往粮仓中,斗了食粮,到朝歌卖了便好,此不比笊篱强上不少。”宋异人听之大笑道,“愚兄不才,或是旁物缺失,这钱财最为不缺。”
姜子牙听之,自是拜谢,马招娣闻有赚钱之道,自也不闹,这一夜折腾不表,只说来日方明,姜尚便挑了面斗,直往朝歌而去,不多时果然有人来问:“卖面的,你这食粮如何变卖?”
听人询问,姜子牙顿时打了一个精神,心道,开市的来了,急忙回到:“您要多少面。”
那人嘿嘿一笑,拿将出一个铜板:“来一文钱的。”
“你……”姜子牙心道,买面如何有这种买法,心中自是不顺,可今天若不将些银两回去,家中之人,更是难以应对,无奈之下,只好低头称面,“客观稍等,不时便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