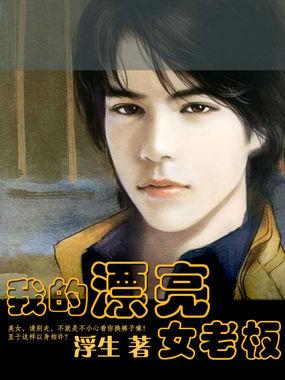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写战犯改造的电视剧 > 第61章(第1页)
第61章(第1页)
他是湘西石门山区长大的,十来岁时,母亲叫他送点东西给外婆去,一个小孩走山路,白天一般是没有多大危险,但那天他正走着,刚一拐弯,迎面看到了一只大老虎,这种华南虎吃掉一个小孩是很平常的事,所以他一看到老虎出现在面前,便大叫一声哭了起来,同时把手中的小竹篮向前一扔,正好篮子里装的东西是用红纸包的,老虎听见一声大叫已有点惊慌,又看到扔出一团红色的东西,便掉头就跑。他愣了一下之后,也边哭边向家中跑。从那以后,全村子里的人认为白天出来找东西吃的必定是饿虎,小孩遇到饿虎而没被吃掉,肯定是这小孩命大福大,所以后来他长大果真当了将军。
既是命大福大之人为什么会被判死刑,差一点就绑赴刑场?我非问个明白不可!
困兽
我一向好奇,便向他寻根问底,他也很坦白地告诉我,为什么他和另外三个人会被判刑的主要原因。
原来在有名的&ldo;徐蚌会战&rdo;(解放军称为淮海战役)中,他所在的12兵团从1948年11月23日开始与解放军接触,经过20多天激战,到12月10日以后,原来归12兵团指挥的四个军只剩下18军和10军了。而10军所属的114师因伤亡惨重,奉命将所守的村庄放弃,整顿了一下残存兵力,便在安徽蒙城、宿县之间的双堆集东侧的开阔地建立了一个野堡阵地,以掩护北面的兵团司令部。两天后,这个师的54团在解放军强大炮火猛轰和精锐部队突击下全团被歼灭,该军所属75师一个团长阵亡,另一个团长则放弃阵地,被宣判当场枪决了,这样士气才被迫略有振作,虽然被打得疲惫不堪但还是与解放军逐屋争夺。最后在双堆集东南的尖谷堆制高点,使用了毒瓦斯弹,因解放军没有防毒面具,死伤相当多。但解放军的包围圈却越来越缩小,几万人的粮食全靠空投,弹药也要空投,有时降落伞坏了,投下的东西打死打伤不少人。最后空投的大米、面粉因没有燃料不能煮熟,便请求空投烧饼、馒头等熟食。一包东西投下来,饿慌了的士兵便去抢,怎么下令也制止不住,结果空投变成了内部斗争,有时为了一袋食品,相互开枪打起来,死伤不少。士兵和下级军官天天在为吃饱肚皮而你争我夺,哪里还有什么心思去打仗,特别是他们看到那些高级指挥官照常有吃有喝,更加怨恨。有些士兵便把马杀了用白开水煮了吃,没有燃料便拆门窗,最后连棺材都挖出来劈了当柴烧。
解放军对被包围的部队一面用扩音器喊话,一面用门板等写上很大的&ldo;优待俘虏&rdo;等标语竖在前沿战地上。士兵和下级军官看了更不想再拼命,不少人暗地里去向包围的解放军要东西吃,要到之后又跑回自己的战壕来。特别是许多被俘的士兵和下级军官不少被释放回来,大谈解放军如何优待俘虏,这样更加使士气动摇。连许多高级指挥官对邯郸cp广播电台播出洪亮的声音,都存在既想听又怕听的矛盾心理。
被俘
被围困的许多师长、军长,以及兵团司令都收到被俘释放的士兵和下级军官悄悄带回给他们的劝降信,有的是起义、投诚的熟人写的,有的是解放军政治部门印发的。这更使这些将领们相互之间增加了猜忌,互不信任。最后便下令不准被俘的人员通过前沿阵地回来,凡是硬要进来的便开枪射击。
当包围圈越缩越小,几次企图突围而没有成功,解放军的喊话筒便一再警告,不准破坏武器,破坏武器者被俘后要受到严厉处罚。所以黄维、胡琏再三命令,要在准备最后拼命突围时,一定要把带不动的重武器、弹药全部破坏,但下面执行都有顾虑,怕被俘后解放军要追查,因为都估计突不出去的成分占多半。能突出去的希望很少,所以在破坏武器时都是敷衍了事,更有些人是有意保留下来准备能完整地保存至被俘后缴出立功,至少不会受罚。所以到最后一次集中全力突围时,除了胡琏和几名将领冲了出去外,黄维、覃道善、十八军军长杨伯涛等十二兵团的军师长,基本上都成了俘虏。
据说黄维在被俘后,从双堆集移解到浍河以北一个村庄小住时,有个解放军青年干部质问黄维:为什么不服从解放军命令老早投降?黄维大发脾气,冲着那个干部骂了一通。那个干部气愤愤地走了。还有几个战地随军记者要给他们照相,多次都没有能照好,因为都不愿让他们照。这几个记者也很恼火。这时,覃道善有点担心,害迫马上会引起严重后果,甚至有被杀害的可能。他睡上床,鼾也打不起来,因心里有事睡不着。结果几天过去了,也没有人找他们的麻烦,照样是四菜一汤的小灶饭。
到第二次起解,在徐州北面的韩庄车站,押送俘虏的车停下上水上煤时,附近一个解放军的野战医院中大批伤残人员,一听说这一列车厢中有十二兵团被俘的高级将领,便愤怒异常地一下集中了两三百人,包围着车厢,大声鼓噪叫喊,要就地处决他们。覃道善吓得站都站不起来,押送的干部一再说服这些伤员,他们就是不走,火车也无法开走。最后经医院负责人和押送干部向这些人交代了政策,并答应把这些人押出来给他们看一下,条件是不准当面辱骂和投掷石块等,负伤的指战员们才勉强同意了。覃道善不敢出去,最后是由黄维、杨伯涛两人站在车厢门口,让这些人看了一下,火车才慢慢离开车站。押送他们的那位解放军是黄埔四期毕业的,对黄维等黄埔同志态度很好,等到车开出韩庄,他才掏出手帕,把额头上急出来的汗珠轻轻擦掉,并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声:&ldo;好险!&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