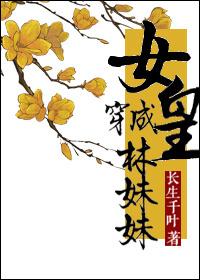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品中国文人好句 > 第135章(第1页)
第135章(第1页)
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称十九世纪法国社会的史诗是比较合适的。这同时也是它的短处:过于现实了。难怪伍尔芙这样的意识流小说大师,毫不留情地批判巴尔扎克,而推崇印象与现实交融的普鲁斯特。
欧美各现代画派,也从不同的方向,给写实主义贴上了封条,将单纯写实彻底送入了美术史。
莫洛亚《追忆逝水年华》的序言中写道:&ldo;像德加或莫奈用丑女人画出杰作一样,普鲁斯特的题材可以是一个老厨娘,一股霉味儿…他对我们说:好好看,世界的全部秘密都藏在这些简单的形式下面了。&rdo;
《红楼梦》的英译者霍克斯曾言:这部古典名着像一本现代小说。
而当下的许多中国小说,重故事情节,轻洞察生存,一件事就是一件事,一张脸就是一张脸,事完了,人也没了……作家似乎走上了回头路。
《红楼梦》通篇用白话,是小说对应日常生活的逻辑结果。说她&ldo;用白话&rdo;,其实也不够准确,不能揭示她与生活的浑成状态。毋宁说,曹雪芹原本是用大白话来思维的,雅俗浑成,北京的官话,吴侬的软语,氤氲在一块儿。专家学者举证多矣,也曾唇枪舌剑,而后达成共识:《红楼梦》的语言,是南北语系水乳交融的典范。当时的北京已是金元明清四朝古都,北京人又羡慕南方的富庶,南方的文化。邓云乡先生指出:&ldo;清代统治者起自关外苦寒之地…极羡慕江南苏、杭一带的风物民情,菜讲南菜,货讲南货,纸讲南纸,酒讲南酒,衣讲南式…就连说话也觉得南方话好听,所以有&lso;吴侬京语美如鸢&rso;的说法,就是说江南人说北京话简直像黄莺叫一样,比北京人说北京话还要好听。&rdo;
也许可以这么讲:南北文化,均汇流于曹公笔下。
曹公在北京写作,记忆冲着南方。他打通了雅俗,涵盖了南北。他的白话文,比&ldo;五四运动&rdo;时期的白话文更流畅。这蕴涵着什么样的大问题呢?
现在,北京有大观园,上海也有大观园。两座风格迥异的大观园,合成一个文化隐喻。建筑艺术家的杰作,对作家是个提醒。
思想层面的《红楼梦》,我略谈几句感想。
清代尊程朱理学,康熙雍正乾隆,封朱熹为&ldo;十哲之一&rdo;。一提理学,大家都会想到&ldo;存天理灭人欲&rdo;、&ldo;天不变,道亦不变&rdo;。清中叶的思想家戴震,以人情、人欲之说抗衡天理,像魏晋竹林七贤,以&ldo;不孝&rdo;与放浪抗衡礼教,二者都对封建统治者玩弄的花招说不。玩弄花招是说:让社会的伦理道德,永远听命于皇权、族权,听命于统治者的意识形态。贾府等级森严,处处道德布控,不独摧残奴婢,连主子也不放过。可见,道德这种东西,一旦僵化,势必祸及方方面面,紧要关头要吃人的。
道德的本质,尚须细思量。
曹雪芹的思想与戴震相近,不过,他重情、重欲、甚至借警幻仙姑的口称贾宝玉是&ldo;天下古今第一淫人&rdo;,则是他从自己的红楼大梦中悟出来的。作品的立意或主题,因回流到日常感觉,所以无板结,无说教。《红楼梦》中的意识流动,似乎到了&ldo;意识流&rdo;的边缘上,却停在边缘,照顾读者。小说开头还谈了一通&ldo;意淫&rdo;,俨然是个大发现。估计雪芹原稿,涉及&ldo;淫&rdo;的东西更多,被脂砚斋斟酌后划去了。
曹雪芹九
天理走了极端,情、欲、色要走另一个极端。这是历史本身的张力使然。
想想曹雪芹那阮藉式的性格,多愁善感又桀骜不驯,他要走极端的。只有那些在一条路上走到黑的人,方能看见飞鸟各投林,&ldo;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rdo;
作家的好手段,是一竿子插到人性深处。插不深,则会弄些面面俱到的拚盘,宣称他表现时代……
宝玉含玉而生,那块玉,王国维解读为欲。人生诸多欲望烦恼,系在脖子上。宝玉摔它好多次,恨声连连,把命根子说成劳什子。他最后看破红尘遁入空门,似乎解决了欲的问题,由色而空,一切人间悲喜,终归于佛门清净。我觉得,这是曹公布下的迷魂阵。由色向空,古今中外皆有,是生存情态中固有的环节,只程度有不同。跛足道士唱的《好了歌》,说世间一切&ldo;好&rdo;都将归于&ldo;了&rdo;。甄士隐有&ldo;夙慧&rdo;,一听便悟,当场为《好了歌》作注解:&ldo;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rdo;不过,官场民间,有此&ldo;夙慧&rdo;者并不少。曹雪芹的高明处,却是把我们的目光定在茫茫雪地上,由空返色,由大梦的终点返回大梦,重新打量人的生存,尤其是女性的生存。他带着我们步入虚无,又从虚无重返人世,这一去一返并非无用功,它使生存的诸环节毕现纷呈。
由色而空,由空返色;从有到无,无中生有:这是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庶几接近西哲所言:&ldo;人是虚无的占位者。&rdo;
而一般作家和思想者,常止步于由色向空的环节。曹雪芹走得更远,这&ldo;更远&rdo;却是返回。修养,情力,欲之烦恼,三个助推器,成就了我们的顶级作家。
曹雪芹确立女性价值,是《红楼梦》的核心思想。群芳凋零,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然而有芹泥,有雪芽;&ldo;一寸嗟独在&rdo;,有叹息就会有生长。有见证毁灭的眼睛,就会有美好的事物重新出现。曹雪芹的人生观是入世的,积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