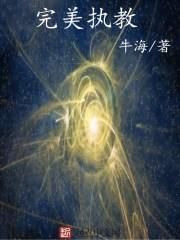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糊涂虫指不明事理的人变色龙笑面虎 > 第82章(第1页)
第82章(第1页)
只见一片星空。唯有船头挂着的灯笼在水面上晃动,像个歪斜的满月。
船近岸边,似乎是回到原先的埠头了。只见那个影子掌柜背对着船屋的灯光,站在栈桥上。
而且,他身旁还有一个女人。
一开始,平四郎还以为是阿律,以为是凑屋或久兵卫叫她来为先前逃离濑户物町道歉。然而,当船嘎吱有声地往栈桥靠近,平四郎便发现那女子的身形是全然陌生的。
年纪不小了‐‐那身和服仿佛映照着星空般,是深色底上散落着白色的花样。
啊,是阿藤‐‐他总算想到了。
女人望向船,却不是在看平四郎,像是看着屋形船的灯光,也像凝望着水面。在有限的照明中,难以看清她细部的表情。也许是平四郎想在当时看到的东西,以他想看到的形式出现了而已。
即使如此,平四郎也不知道自己想看些什么,不明白自己在期待些什么。因此,阿藤理应仍是个大美人,却怎么也看不出。若跳进水里,一定会就这么变成水吧。
她定是来迎接总右卫门的。阿藤走到栈桥的最前端,等候屋形船停靠。船离岸还有三尺以上,平四郎却嘿的一声,从船上跳下来。阿藤向平四郎行礼,平四郎却快步离去。
然后,他才总算醒悟到,啊,原来凑屋总右卫门是要让我看看阿藤长什么样子,觉得一定得让我见上一面,好证实他自己的说法吧。
「相公。」耳里听到她喊总右卫门的声音。之后,又短短说了几句,却听不清。
是寒冷的河风吗?还是阿藤的声音触动了内心?骤然间,平四郎心想,在凑屋总右卫门冷硬的表情之后,确实隐藏了愧对阿藤的念头,或许就只有那么一丝丝、不仔细找寻便无法察觉。不惜沾惹那些麻烦,演那种愚蠢至极的戏,动用劳烦那么多人,花了大笔银子,就为了要在阿藤面前隐瞒事实,配合她所深信的误会。而总右卫门会这么做,不单单是为了保护葵,也是对阿藤有那么一点恻隐之心吧。
也许只是平四郎希望他有而已。
平四郎快步向前,身后却传来追赶的足音。他头也不回地丢下一句「我不坐轿子」。
「井筒大爷!」
是久兵卫喘着气追上来。
「该说的都说完了。」
久兵卫气喘吁吁地停下。平四郎放慢了脚步,却没有停。
「我走了。」
距离渐渐拉开。
「请大爷原谅。」久兵卫说道。
「没什么好原谅的啊。」
平四郎没有回头。
「那是你尊敬的主人不是吗。你理当为他效力,不必向我道歉。」
这倒是真的‐‐他在心底说。
腰好痛。
过了两天,有个老人来访,说是为住在千驮谷小旅店的佐吉传信。老人的亲人在那位大夫那里看病,家住浅草。平四郎向老人道谢,要细君请他吃饭,并趁着这段时间看佐吉的来信。信很短。
大夫收留了久米,阿德陪着她,顺便也看顾其他女子,帮忙煮饭。患者实在太多,人手不足,因此佐吉也帮着做些砍柴的粗活,以致耽误了归期。
大夫诊察的结果,久米的日子大概不多了。阿德说至少要陪她到最后。佐吉则预备几天后要先回深川一趟,因为必须去找凑屋商量,帮阿德另觅住处。
望着那条理分明的文笔、工整的笔致,平四郎下了决心。
佐吉只要过他自己的日子就好。要让他过自己的日子,最好是别再翻旧帐。不久的将来,他会有自己的家室,待生下孩子,更会是独当一面的男人;这么一来,他的人生便完全属于他自己,没有必要此时还去搅乱。只愿那个叫阿惠的姑娘,是个如同上天恩赐的好姑娘。
老人明天便将再行前往千驮谷,平四郎便随手写了一句「这里一切如常」的短笺,交给老人。然后,带着小平次出门去。
傍晚,到奉行所办公后回宿舍的路上,平四郎稍微绊了一下。竹皮草屐不知踢到了什么,总之,真的只是微微颠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