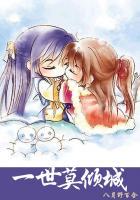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红白喜事四言八句顺口溜 > 第102章(第1页)
第102章(第1页)
段一帆回忆着,眼神空洞而茫然,“我父亲已经死了,但我知道我的恐惧还在。我昨天晚上又做了那个噩梦,我梦到我被脱光了衣服,戴上了狗链,关进了一个笼子里。笼子里是对我露出獠牙,流着口水的野兽。笼子外,是看着热闹指指点点的人群。当我被撕咬的时候,笼子外的人却在拍手叫好!我看不清楚那些人的脸,因为他们的脸狰狞而变形,但是你却知道他们跟你一样都是人,但他们又跟你不一样,因为他们的脑子被邪恶吞噬了,只有你一个人清醒着,却遭遇着非人的待遇!”
“你在笼子里面与野兽搏斗,但脖颈的铁链却桎梏着你,你没有武器,更没有力气,你根本就打不过这只野兽。从小到大,我每一次的噩梦都是这样的场景,最后一幕就是,这只野兽用他冰冷的眼神注视着我,当他张开血盆大口向我扑来的时候,我就突然惊醒了……”
讲述完这个梦境,段一帆摘掉眼镜,揉了揉眉心,他看起来很疲惫,好像讲述的过程不亚于和野兽又打了一架。
洪劲妮认真地听着,此刻,她就像一个走钢索的人,顺着段一帆的话小心地寻找通向他心底的那根绳索。
“那只野兽是你的父亲,而笼子里的人是你?”
“不。”
段一帆的声音冰冷而决绝,“笼子里的人是我的母亲。”
洪劲妮困惑地看着段一帆,他重新戴上了眼镜,连镜片都抵挡不住他眼中的灼灼怒意。
他深吸一口气,一字一句道,“我的母亲是被拐来,卖给我父亲的。而我是一个人贩子的儿子,一个强奸犯的儿子。”
46我们都要学会不害怕这个世界,不再害怕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一切。
这一刻,洪劲妮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昨天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她会觉得如此不和谐。
照片中的男女看上去完全不像是夫妻,那个女人的眼睛里只有想要逃离的恐惧和无助的绝望,那个男人的脸上挂着令人作呕的笑容,眼睛里尽是贪婪和欲望。
段一帆轻抚着照片里的女人,娓娓道来,“我的母亲贾晓玫,是一个大学生。她在火车站帮助了一个体弱的老年人,但谁能想到那个人竟然是个人贩子!他把我的母亲拐到了我父亲的村里,转手卖给了我父亲。那个村子被大山阻隔,封闭又无知,被拐来的女人连畜生都不如。但我的母亲本来也是个被捧在掌心里长大的孩子,她做错了什么?她不过是比别人更善良一点,所以就被人贩子选中了,你说,这世上的事多么不公平?”
段一帆说到这里,不禁冷笑,但眼神却充满了愤恨。
“我母亲被强暴以后,就怀了我,或许我根本就不应该生下来。我生下来以后,最开始的时候,我父亲对我很好,因为我是个男孩。他觉得他在这个村子里可以抬起头了,他们老段家生了一个儿子,真是了不起呀!”段一帆说着发出嘲讽的笑声。
“然后,我开始读书认字,直到有一天,我发现关着我母亲的那间柴房里,写满了我母亲用鲜血写下的触目惊心的两个大字——回家!我那时才意识到,这个像猪窝一样的地方,根本不是我母亲的家。她告诉我,她的家在很远的地方。从那以后,我就每天放学趁着我父亲还没回来的时候,偷偷去找我母亲。我母亲哭着给我讲她遭遇的一切,她教育我一定要考出那个地方,离开我父亲的魔爪……”
段一帆讲到这里,带着自责道,“可我当时太天真了,竟然去找我的邻居帮忙。跟他们说救救我母亲,你知道结果是什么吗?”
洪劲妮眼神微动,她已经猜到了,那个地方的人无非是一个犯罪共同体。
段一帆冷笑一声,“他们居然把我和我母亲抓了回来,我父亲把我们狠狠打了一顿。那是我父亲第一次打我,打得可真狠呐,我一个礼拜都没起来去上学。从那以后,我父亲开始经常打我,因为他发现我跟我母亲是一伙的,他发现我融不进那个村子,融不进他们靠吃女人活下去的犯罪团伙。所以他试图用武力来驯服我,很显然,他失败了。因为我的身上还有我母亲的意识,我真庆幸,我还有一个虽然身处困境,但依然向往光明的母亲……”
每当段一帆说道自己母亲的时候,他隔着镜片的眼眸,都会闪出如火花般转瞬即逝的光芒。
“后来我母亲又怀孕了,我父亲终于不再打她了。那九个月过得风平浪静,直到我母亲生产的时候,因为难产,我妹妹刚出生就死了。我母亲也受了打击,每到晚上的时候就变得神志不清,我父亲就用一根铁链拴住了她的脖子,像狗一样……”
段一帆咬着牙问道,“你明白那种感觉吗?那根铁链不仅仅拴着我的母亲,它拴住了每一个想反抗的人,也包括我。直到后来,我都在怀疑,我的妹妹到底是怎么死的,真的是因为难产吗?还是因为,她是一个女孩呢?”
段一帆的嘴角划过淡薄的笑意,“而我为什么会活着呢?是不是因为我是一个男孩呢?”
“我母亲的精神因为这件事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我只能趁着她清醒的时候去找她。于是我跟我母亲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我假装顺从,向我父亲靠拢,因为我需要钱,我必须要读书,才能够离开那个地方。我就拼了命的学习,当我再大一点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没有办法再打我的母亲了,因为我的力量可以与他抗衡,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养出来的儿子居然还会还手。”h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