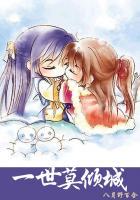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天下为聘6漫画 > 第66页(第1页)
第66页(第1页)
仙家不容得罪,他帝王的威严也不容侵犯,唯一的办法,就是抹去那些污点。他本来应该成功了,那个女人死了,孔家也没了,可是那个妖物,对…就是妖物!竟然杀不死!什么方法都没用,就算是托仙家带来上界的□□也只是要了他半条命而已。“这一切都是那个妖物导致的。若不是他迷惑我,表现出可能有灵根的样子,我怎么会如此,怎么会有如此结果!一切都是那个妖物的错!”苍炎帝似乎找见了合理的借口,一句句吐出这些伤人的话。最后竟然自己还深信不疑。孔景荣快被气笑了,这么无耻的男人,当初他的好妹妹竟然觉得他是良人?长亭那个孩子经历了什么,以为他这个当舅舅的什么都不知道?“陛下,这些,您还是留着在剩下的日子慢慢说吧。”从袖子里掏出匕首,一步一步走到苍炎帝身边,蹲下轻问到:“浑身使不上力气吧?放心,那种药不会要你的命。”他本来是打算毒死这个男人,可外甥的一封信让他打消了注意。他觉得,那个方式,更适合惩罚这个人渣。拿下架子上摆放的袜子,塞到苍炎帝的嘴里:“您慢慢享受,接下来,只是开胃菜。”血色溅上龙床的帷幔,孔景荣就这样慢条斯理地废掉了苍炎帝的手脚,好像在画一幅画,如此风雅。孟长亭站在苍炎帝的寝殿门外,身前的门框已经被他压出了凹痕。陆迁把他的手拉下,包在手心。轻轻环住他的阿柳,陆迁低头在孟长亭耳边说到:“你很好。不是你的错。”孟长亭咬住下唇,闭上眼任由男人的气息把他包裹起来,半晌才低低地应了一声:“嗯。”登基流炎城的一个阴暗的小巷中,有个人卷着一张草席在冷风中瑟瑟发抖。虽是初春,可没有厚衣敝体,依然能感觉凉意。这个乞丐的手脚似乎都不能用,只能靠膝肘爬行着向前挪。一缕缕的脏发遮盖了他的面容,身上穿着的破旧麻衣也丝毫看不出他的过去。每当有人走过这个阴暗的小巷,都会躲得远点,生怕传染上什么不好的东西。更有小孩那石头砸他,说他是叫花子,是乞丐。一开始,这个人还会生气,不能说话的嘴里发出嗬嗬的声音,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开始变得有些疯狂,用头猛地撞击墙面,去寻死,去跳河,却总是死不了。就算是不吃饭,也有人把他救回来,就是不让他死去。最后,男人也麻木了。只是坐在这个角落里对着不远处巍峨的皇城发呆。也有人看他可怜,给他银钱和食物,却在下一刻就会被别的乞丐抢走。甲一从门外走进来,跪在孟长亭的桌案前:“回陛下,那个人目前还活着。”孟长亭放下手里的奏折,“知道了。看好他,切勿让他离开你们的视线。一定让他‘好好’活下去,亲眼看着朕把这苍炎变个模样。”那个人做不到的,他孟长亭能做到。“是。”甲一领命退去。一个人站在这御书房里,孟长亭看向窗外。让一个做过帝王的人去当乞丐,消磨他的尊严和傲骨,才是最残酷的惩罚。尤其是要面子的人,这无疑,比取了他性命还要痛苦的多。皇宫里的宫人们又忙碌起来。过几天就是新皇登基的时候,要是出什么纰漏,说不定就要了他们的小命。这个新皇,可不是个好惹得,听宫中的老人说,以前的罪过新皇的人,都不明不白的死了。以前还不知道,最近才有人将二者的关系联系起来,顿时惊出一身冷汗。好在当年他们没有作死,否则真的死了也不知道为什么。*流炎城外有一座岩山,直上云霄,自古以来就是苍炎皇族祭天之所,上有云台,名曰天炎。今日正逢黄道吉日,百官皆身着礼服,手持玉笏,跟着三家供奉向天炎山走去。街上百姓驻足围观,却不同于以往的热闹。个个肃穆而立,目送朝臣远去。倒不是这些百姓对新皇有多高的期待,而是因为每次祭天,仙家都要沟通天地,保佑苍炎能够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他们怕高声喧哗会惊怒诸天神佛,失了庇佑。今天的天色如此阴沉,也不知这祭天能否顺利进行。有仙家……应是无碍?众人来到山下,三位仙家供奉登上法坛。上面早已陈列好做法的用具,只等时辰到,天子上云台祭天时,就开坛做法。乐者早已准备妥当,待天子座驾临近,丝竹之声顿起,伴随编钟空灵玄妙的声音,悠然向四周荡开。陆迁勒停拉车的马匹,跃下辕座,亲自为阿柳打开箱门,放下脚凳将人扶下车来。看到赶来的宁可为,唇线微抿,一身冷气地将孟长亭的手交给他。若不是他不得暴露身份,这引领天子祭天一事,怎能落到这个新任的太监总管身上。孟长亭瞥了陆醋坛一眼,觉得有趣。谁能想到不苟言笑,面无表情的苍炎战神陆将军会是一个陈年醋坛?那得惊掉多少人的下巴。不过,他喜欢。走过安置金椅的高台,踏上那被历任帝王磨得平润的石阶。拾阶而上,视野渐渐开阔。城楼,屋舍,阡陌,远山,待半个时辰过去,这九千九百九十九阶登天梯也只走了一半。纵使脚步变得沉重,孟长亭也不曾停下,反而有些沉静在这种感觉中。身体的疲惫仿若为了得到这皇位而经历的苦痛,但一步步前行才是他能来到这里的原因。未到顶端,他便不会放弃。就这样慢慢把山河尽览眼底,俯阅风云,怎能不是一种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