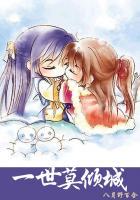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蒹葭彩彩下一句 > 第八十二章 侥幸(第1页)
第八十二章 侥幸(第1页)
琴泣难得扑哧笑出声,眉眼如画,扰得姜太傅又一阵失神,
“琴泣一介贱籍怎会与皇家媳交好,不过是结份善缘罢了,哪想琴泣还未有事相求,她就落魄至此。”
顿了顿,端正了神色,恢复了往日的语气,继续说道:“那日她救我一次,虽是她自作多情,但亦是我欠了她的,琴泣乃微末之人,不愿欠人恩情,唯恐来生衔草结环相报,还请大人留此女一命,祁家已亡,东宫亦无威胁,如此也显得大人宽厚。”
姜太傅眯着眼捻着胡须,喜怒难辨,直直盯着琴泣的面目,琴泣亦神态自若地回望过去,良久,姜太傅捧腹大笑:
“哈哈哈,没想女先生竟是善男信女,老夫从不信因果轮回,宿命报应,若上天真如那些秃驴们说的有好生之德,又为何要让世人受尽疾苦呢?老夫只信自己,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今世远比来生有意义。”
说到这,不掩情欲地看着琴泣继续道:“不过女先生毕竟是女流,信这些也无妨,老夫就为了你留那丫头一命,你可来生莫忘了我。”
最后一句暧昧不清,含混不明的情话若是出子某青年才俊之口也是一段佳事,可惜由着一个半只脚入土的老朽说出除了弄得满室腐败蝇腐之气再无其他。
对着姜太傅躬身行了个万福礼以表谢意,琴泣心中莞尔,来生她要做那顽石浮云再不为人,无灵智之物谈何相忘。
风不停,树影婆娑。
通往县京城的要道上,一个鬼祟的人或做农家老翁模样,或成坡脚樵夫打扮,每每都成功掩藏了身份,隐逆了行迹通过各都城关卡,直到县京城门,两旁守卫搜查甚严,才堪堪慢了脚步。
连日赶路,每日睡不足两个时辰,三餐啃干粮应付着,白净的面上生出错乱的胡茬,漠北的风哨,沿途的日晒,即便熟人见了此时的石熙载也不见得能相认,但保险起见,石熙载仍是在城门外的破庙歇了一宿,难得睡到第一声鸡鸣时分,轻手轻脚起了身,未扰到同宿破庙的乞丐们,去河边漱了口,在周边民居陆陆续续亮起烛火前在抓了把灰抹匀在面上,看着河水中影影绰绰的人像,一拳打碎。
这还是他吗?他看到那黑黢黢的面容下浑浊的神魂,痛苦地闭上双眼,祁家不该走至如此的,都怪他。
在草木的掩映下,石熙载悄声接近城门,此时接近守卫轮班交替之刻,值夜的守卫睁着惺忪的睡眼,困顿地掩唇打着哈欠,等待着第二声鸡鸣交班,正是全身松懈、不加警惕,石熙载就趁着这须臾的空档抛绳勾住城墙壁,几个折返攀上城墙又翻身而下。
城内已有挑货郎揉着眼开始走街,早茶铺子也挂了幡子开张。
石熙载垂首沿暗处蹑步行着,眼神却观察着周围,逐渐苏醒的街巷上有昨日喧闹的痕迹,两旁鳞次栉比的楼宇一眼望不到头,回想起儿时父亲砦禾休沐时常带他来东门玩耍,两三茶摊,几处铺面而已。
如今不到十年光景,却是变迁到他认不出原有模样,怔怔望着酒楼乐坊林立的县京城,这真的是他心心念念想要回到的地方吗?为何踏足此地竟然毫无亲切感……
至一处包子铺,升腾的蒸汽遮盖了店家的脸面,扑面的香气袭来,石熙载停下了脚步,腹中咕噜,囊中羞涩,离开朔方仓促,盘缠已花的七七八八,还要留着银钱以备不时之需,却是许久未吃过热乎饭了。
片刻走神间一只脏兮兮的手将个白白胖胖的包子递到石熙载面前,
“喂,小子,年纪轻轻手脚健全抢老叫花生意可说不过去,给你个肉包吃罢去找个活计做。”
意外于此人能在无所觉察的情况下这么近距离靠近自己,石熙载袖中暗器滑至手中蓄势待发,面前的老叫花却突然笑起来,振聋发聩的笑声在大清早难免惹得行人注目。
这一笑中气十足,俨然不是平常老人该有,石熙载不好再动手,亦知未必是其对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忌惮地盯着老叫花的一举一动一步步往后退着,到了拐角处闪身进了条胡同消失不见。
老叫花瞅着石熙载满是防备地逃离,咬了口手中的包子,含混不清地嘀咕着:
“呀?原是个练家子,倒是老叫花多事了,不过现在的孩子啊,都这么小心翼翼么……”
拳头大的包子不过三两口便下了腹,老叫花餍足地眯起眼,折了个柳枝一边剔着牙一边优哉游哉往城外行去,还有人等他带早饭呢,肉包子凉了可不好吃。
而慌不择路的石熙载拐进胡同后挑着人少僻静处跑,待到确定老叫花没有跟上来后,才发现这一通乱转已失了方向,这里是到了何处呢?
三层高的土楼,看造型当是南边的玩意,他这些年交友甚广,也听闻了京城里颇负盛名的红袖招,一个秦楼楚馆能做到这般程度确实不易。
虽是惊诧红袖招的庞大,但他自心底鄙夷冶叶倡条,更不屑与出入其中的读书人为伍,在朔方便烦透了这种应酬,此刻不愿再在红袖招外多待,正要离开,自那半闭的朱漆大门里出来了一个他毕生难忘的人——那个送他去朔方,告诉他他的仇人是萧太师,日日夜夜出现在他的噩梦中,即使蒙着脸他亦能一眼认出的人。
再见此人,石熙载止不住颤抖,一时也不知是长达数年积累下的恐惧或是有机会再问清楚的喜悦,暗器再次握至手中,掌心的汗**了精巧的袖箭,石熙载瞪大了双眼,一步步向蒙面男子靠近过去。
这处虽在福茹街近处,却清冷异常,周遭静悄悄的,石熙载所闻唯有自己吞咽的声音,走出了暗处,蒙面男子也看到了他,四目相对,蒙面男子却没有识得他这故人,反而全身似猫弓背起来,一手搭在腰间长鞭上,神色警惕,眼周的疤痕显得狰狞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