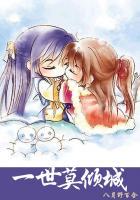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论撩世家子的技巧by墨书白 > 第63页(第1页)
第63页(第1页)
可这样的人因为矛盾难以平衡,在过去蔚岚也不曾怎样遇到,故而仔细想想,谢子臣哪怕是个男人,也是个极有能力的男人。蔚岚过去一向不太看得起男人,然而昨夜的挫败感却让她觉得,这个世界的女人不像女人,这个世界的男人,大概也不是过去的男人。她张合着小扇看着谢子臣,评估着对方,谢子臣察觉的她的目光,抬起头来,淡道:“看什么?”“过去不曾好好看过子臣,”蔚岚微微一笑:“今日特意认真看看。”闻言,谢子臣仍旧静静看她,眼中带着询问,蔚岚只好多加解释:“过去看子臣,只觉得子臣是个美人。如今看子臣,却才发现,子臣也是个能人。”谢子臣没说话,皱起眉头想了片刻,却是问:“发生了什么?”蔚岚微微一愣,这人心思太快太敏锐,竟让她一时不防,接不上话来。谢子臣放下书来,给蔚岚倒了杯茶,蔚岚随意坐在蒲团上,看着那茶水落入杯中,被美人推至面前。“你说,我听着。”谢子臣淡然开口,蔚岚端起茶来,抿了一口。这个人似乎有种安定人心的力量,就这么端端正正往你面前一坐,你就觉得所有事情,似乎都并不是无法解决的。茶水入口,清香中带着苦涩,又在舌尖百转千回,转出了丝丝甘甜。蔚岚一直伤怀的心得了舒展,她持茶含笑,低声道:“如君所言,岚的确被一事所惑。”谢子臣没说话,按着广袖,给蔚岚填茶。蔚岚转头看着窗外已经零落的桃花,慢慢道:“我曾有一信念,虽众人都说不对,我却仍旧坚持。我以为凭借我一人,至少能扭转此局面半分,最终却发现,无论如何,此事也难以回转。若难以回转,在下此生,怕都要活在心结之中。”让她一辈子面对这些想着男尊女卑且不能改变的人,她就觉得绝望。谢子臣瞧着她的模样,转念一想,便道:“是桓衡吧。”蔚岚微微一愣,随后不由得笑开:“君料事如神也。”“你投注心力在桓衡身上,却发现桓衡与你想的全然不一样,于是你就觉得,自己再如何努力,怕也不能让别人按照自己所想去改变。”谢子臣将茶碗中的茶叶拨弄出来,倒入一旁的框中,垂下眉眼:“可是阿岚又怎知,自己一定是对的呢?”说着,谢子臣抬起漂亮的眼,目光中一片淡然:“若是错的,又为何让别人去改变?”蔚岚没有说话,陷入了沉思之间。男尊女卑是错的,那她所想的女尊男卑,又是对的?“阿岚可知这世上最公正的是什么?”谢子臣再问,煮沸热水,将茶叶拨弄至茶壶中,蔚岚静候着他的答案,听他道:“是时间。”“君可不必自扰,你觉得什么是对的,你就继续坚持,十年二十年后,你便会发现,对的都会留下,错的都会改变。这世间会迷惑一时,却不会长长久久的迷惑下去。你坚持你的,他坚持他的,所谓想法,本就该百家争鸣,只要不去强逼着对方做什么,那就无碍。”“若你如此想,逼迫着别人也如此想,那是你的不是。为人立身,管好自己,便足够了。”说着,谢子臣忍不住笑起来,抬起漂亮的眉眼,将刚好倒出来的茶递到蔚岚面前:“这也是阿岚,前些时日教会在下的。”听到这话,蔚岚没有言语,她低头看着对方端过来的绿汤,片刻后,朗笑出声,接过茶碗后,双手捧着茶碗,恭敬行了一礼,认真道:“谢过子臣,是岚狭隘了。”谢子臣点点头:“是狭隘了些。”蔚岚:“……”给个杆子就往上爬了。“我为阿岚解惑,阿岚也为我解一惑吧。”谢子臣放下茶杯,抬头看着蔚岚,眼中全是认真。“在下倾慕一个人,但若要和此人在一起,却要牺牲太多,在下放不下,舍不了,逃不开,却又不舍得拿一切去换这份感情,君以为该当如何?”听到这话,蔚岚不由得笑了:“子臣有心上人了?”谢子臣没说话,片刻后,郑重点头。蔚岚放下茶碗,含笑道:“感情之事,随心尔。你不愿以有的一切去换这份感情,不过是因这份感情没有到需要你换的程度,既然没有到,那就不用强求。默默喜欢对方,不也是一件极让人欢喜之事吗?”“若那人一生可能都不喜欢你呢?对方无法回应你的感情,也不会回应你的感情。”谢子臣静静凝视着她,蔚岚张合着折扇:“我以为,子臣是遇见想要的,就会伸手去拿的人。喜不喜欢你,至少要得试试,等待一份感情,也同狩猎差不多。”蔚岚给谢子臣传授着经验,完全将对方当做了同性一般:“你要慢慢等待,引诱,围剿,收网。你要捕的是只兔子还是老虎,是只鹿还是狼,不同的动物,不同的策略。花上耐心,”蔚岚抬头微笑:“斩了所有荆棘阻拦,将她逼到避无可避,再收网捉鱼。”“到时候,若她还拒绝你,这也算你努力过,不过是少年一场风流尔,回首仍可笑谈中。”谢子臣没说话,他点点头,端起茶碗,举杯恭敬的行了一礼。当他抬起头来,同蔚岚含笑的眼对视在一起,两人不由得相视一笑,朗声开怀。当天夜里,众人又小聚一番,归去时,桓衡小心翼翼跟在蔚岚身后,蔚岚酒意甚高,将手拢在袖间,踏着木屐而行,时不时抬头仰望星辰明月,一回头看见桓衡那忐忑的表情,不由得笑了:“阿衡本是豪爽男儿,怎的学得如此姿态了?”“阿岚……”桓衡抬起头来,有些不安道:“你可还生气?”蔚岚摇了摇头,舒了一口气道:“本就是我狭隘了,哪里还会生气,阿衡莫要过多担心,我已想明白了。我若是对的,你自然会听。你不愿听的,我强求了,那也于你无益。”“我……”桓衡着急开口,蔚岚用扇子止住他的言语,温和道:“我并非气话,而是真心。于我心中,你是出生入死的兄弟,我想要你过得好,故而对你多加干涉,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本就是我的不是,我该同你道歉。只是你一向待我诚心,顾忌我太多,哪怕明明是我的不对,你也会为我改变。是我没有好好重视你的情谊。”“阿衡,”蔚岚静静看着他:“如你想要的去活。无论如何,你在蔚岚心中,始终是那个与我一同杀伐战场、与我生死相交的桓衡。我的愿望,从来都是你活得好,而不是为我活得好。”桓衡听着蔚岚的话愣了愣,好半天,他却是笑了起来:“我知道的。”他说得无比郑重:“我知道你对我,一直是极好,极好的。”蔚岚没说话,她忍不住伸出手,揉了揉他的头发。春日很快过去,迎来盛夏,夏日温度一日高过一日,众人上课的地方也就从北雍宫改到了水榭中,用冰块镇着扇风,终于让大家舒服了些。课程由浅入深,大家都有些不堪重负,每日一面熬着夜一面走着神,唯有谢子臣和蔚岚两人,每日按时就寝,按时起床。那日交谈后,谢子臣脾气好了许多,总不算像之前一样随时暴躁,虽然仍旧在偶尔之间怼上那么一两句,但尚在可接受范围内,众人已经十分感激谢子臣嘴下留情。课程进度加上来,最苦的就是桓衡,每天都在下课之后要蔚岚单独开小灶,谢子臣看不下去,便同蔚岚两人轮流着教导桓衡,蔚岚替桓衡抄书,谢子臣就讲课;谢子臣抄书,蔚岚就讲课。一时间,三人感情到好上了许多。六月时,徐城经历了百年难遇的大雨,好在张御史在三月末就参奏了徐城水利贪污一时,上上下下彻查之后,特意让工部员外郎卫秋前去监察连赶三月,修上了新的堤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