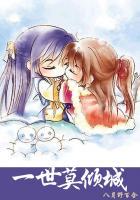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七月与小火焰 > 第5章(第1页)
第5章(第1页)
电梯一直下去,我心口很闷,有种想呕吐的感觉,这次回去的寂寞,这种无边无涯的寂寞。父母亲都老了,加在一起一百四十岁,他们吃饭,他们看报,他们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无边无涯的寂寞,只有一架电视机日日夜夜的哭哭啼啼,那种寂寞。
到了楼下,我靠在墙上,那种寂寞,我会甘心吗?那样子可怕的寂寞:永恒的。是的,他不爱我,但是又有谁爱我呢?是的,他不是结婚的对象,但是,目前谁又是结婚的对象?
跟他在一起累死总比自己一个人闷死好。我闷过,那种排山倒海的闷。父亲的眼睛只看着电视机,母亲的眼睛有时候会淡淡的看着我,我的痛苦与伤心足足与她隔了五十年,她不能明白,她伤了我的心,至死也不承认。
我能到什么地方去?
我挽着箱子上楼,我还是留下来吧,女人受点小气算什么?谁叫咱们生为女人,可是冲到楼上,发觉大门是虚掩着的,我吓一跳,我的天,难道刚才我忘了关大门,一推之下,发觉小道在屋子里。
我拿着箱子当场僵住了,他在翻抽屉找文件,看见我,他说:「我忘了一张合同,回来拿,你失魂落魄的干什么?」
我把东西都收拾走了,他竟问我干什么!他居然没有发觉屋子里一切属于我的东西都不见了,这个人不是粗心,而是卑鄙。
呵小道,我的要求已经降低到可耻的地步了,只要你给我一点点自尊,注意我的存在,一个女人就是一个女人,女人需要关怀,就象花需要雨露一样。
他忽然看见我手上的箱子了,脸上一变,「什么,你提只箱子做什么?收拾东西走?你要走?你少玩点花样好不好,我已经够忙的了,你要我怎么样对你?把你哄回来?我的天,琉璃,你的年龄也不小了,我当初看中你,也就是因为你这份洒脱,现在你居然跟新舞女一样!你要恐吓我?」他取到文件,匆匆地走了。
我呆在那里。
多么的不幸,他几时在这种时间回来过?他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我放下行李改变主意的那一刻回来了,看我这运气!如果他看见之后表示惋惜,他只要说一句:「琉璃,不要这样子,一切等我回来再说。」我马上会抓住这句话下台,但是他没有,他把我好好的讽刺了一下,然后在半夜头也不回的再去办他的事去了。
我也是个大学生,我也受过教育。他对我不能够以这种态度。
我坐下来,倒了一杯酒,这休假算是倒足了霉的休假,算是第几流的休假,我缓缓的喝着,一杯又一杯,然后哭了,露台外边,那条路的灯光仍然灿烂,只是人的心已经变了。
词里有一句叫「寄语薄情郎,粉香和泪泣」。我们都没到那种境界,我是不搽粉的,小道是最无情的。我们要分便分,要合便合,简单得很。
我竟喝醉了。我这样失望的收拾东西离开这个地方,他视我为恐吓他的一种手段,我真有如此低级吗?既然他这么想,那我是非走不可了。算是一时冲动也好,反正我没有这个福份。
但是酒意太浓,我和衣倒在床上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是十二点半。中午十二点半。他没有来一个电话,电话铃未尝响过一下,他人也没回来睡过。我只觉得麻木。人不论男女是越来越凉薄了。为什么不呢?我既然可以随时走路,为什么他不可以也表演失踪。只不过他忽视了一点,我并不是做戏给他看,我拾起东西,马上离开了那层公寓。
到了父母的家,母亲矮而胖的身型跌跌撞撞的出来为我开门,她的耳朵有聋,但是不肯承认,不肯戴助听机,因此与她说话要大声吼叫,为了省力,不如不说。即使她听见了也是没用,如果我说我心中难过,她会答:「有衣穿有饭吃,难过什么?」或是「难过?看医生去。」小道若是温柔点,不失是一个好医生,母亲要是温柔点,我根本不必到处急急的抓男朋友。
我呆坐一刻,回房间去了。
两个多月没住的房间,多多少少有点霉气,我看着那张熟悉的天津地毯,那一堂当年买的红木家具。我真是落泊落难了,如今迁就小道都迁就成这样,早一点受这种委屈,恐怕已经子孙满堂,还听他的废话呢。
我叹一口气,累得不得了,那几只箱子有那么重,一个人抬上抬下,多少次了,难为了箱子,也难为我。好了,从此之后,小道这个人将在我心中一笔勾销,没认识他之前,我在呼吸我在活,与他分手之后,我也还是呼吸还是活,谁没有谁都得活下去的。从今以后,他的明日后日与我没有关系了。
寂寞压上来,黑暗的寂寞,我连忙吞服镇静剂,手是颤抖的,连忙又倒酒喝。应该请假一日,但是请假有什么用呢?我能做些什么?
我洗一个脸,梳好头,还是上班去了,这样一天又一天,白了人头,还没注意春天来到,春天已经过去了,在计程车里我木着一张脸,肩膀都抬不起来,岁月压成我这样子,不良的岁月,来日苦多。
八个小时的工作,每天打烊的时候由我去把灯一盏盏的熄灭,摸在熟悉的灯掣上,昨天譬如今天,今天譬如明天,没有一点的分别。
推开大门,一个人迎上来,我以为是小道,心中一跳,倒有点欢欣,虽然不知道该有怎么样的反应才对,但是至少他来了,他重视我。
但是这个人走近,我马上晓得他不是小道,心往下沉一沉。忽然我微笑了,呀,毕竟我是在乎的,我在乎的不是小道,而是自尊。
「下班了?」那人问。
在黑暗中我问:「李先生?」小道的爸爸?我太惊异了。
「是的。」他说:「要不要去喝杯咖啡?累不累?」
「还过得去。」我说。
他在灯光下看我的面色,「怎么?跟小道吵架了?」
「我早过了吵架的年纪了,我与令郎已经完了。他的毛病是不知道适可而止,哗啦哗啦,令人神经衰弱,还自以为是,认为他道理亨通。」我淡淡的说:「我对他那套理论听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