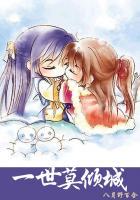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2017年河南省中考作文 > 第69章(第1页)
第69章(第1页)
走廊上全是积水和鞋印,几棵绿色观景盆栽出现在一角,绿油油的。
她曾经最喜欢春天。
因为在春天,田野里种满玫瑰和理想,连河边的柳絮都在漫天飞舞。
压制住胃里的搅动,手心不断泛着汗渍,和雨水混在一起。
她看着急救室的门一点一点合上,站在走廊上,像一只小小的、无家可归的小流浪狗。
有个老大爷看不下去,轻轻叹口气,“小姑娘,先回去换套衣服吧,感冒了家里人会心疼。”
姜春手忙脚乱地拧着湿漉漉的衣服,怎么也拧不干,衣角还在滴答滴答地往下滴水。
有好心的护士姐姐走过来,给她递了件外套,绒布的棉很温暖。
小姑娘发着抖接过,身上没有一点温度,牙齿早已冷得打颤。
急救室里头没有半点声音,姜春的脊背贴着墙壁站着,半步都不敢离开。
心酸的哭声回荡在走廊,医生和护士推着担架床小跑,刚刚那个递衣服的护士姐姐很快跑过去。
架子上的女人腹部鼓起,大得惊人,鲜红的血染透白布,嘴里低低的□□。花白的老人佝偻着身子,木质拐杖一下一下敲在地上,急喘着粗气跟在后面。
在安静的走廊里,洁白的瓷砖很干净,低低的啜泣声很快消失不见。这种平凡而又绝望的现实当中,一瞬便是天人永隔。生离死别的痛。
看见这一幕,她慢慢蹲下身子,环住膝头,拼命抱紧自己,小小的身子发着抖。
小姑娘瑟缩在一角,很轻很瘦,仿佛下一秒就要消失不见。让人不由得怀疑,这样的身板着要有多坚强,才能足够在这世间好好的活下去。
急救室的门口,病患和医护来来往往,装药品的小推车推过一遍又一遍。
面前的玻璃大门紧闭,拉上厚厚的窗帘,窥探不到分毫讯息,尽头的玻璃窗传来的惊雷一声比一声大,穿破天穹,直震山头。
过了很久,门上的红灯灭了。
她撑着膝头站起来,有点胆怯。
医生穿着绿色的防护服,解下口罩,露出来一本正经的国字脸,“哪位是朱蒨的家属?”
“这里!”姜春吸了吸通红的鼻头,沙哑着声。
一个瘦弱的小姑娘跑过来,看上去还没成年,医生想都不想就开口:“小姑娘,跟你其他的家人联系一下吧,这可不是小问题。”
“没有其他人了,只有我。”
她整理好慌乱的情绪,红着眼。
他在急诊科待了十几年,每天都在边缘线上和死神抢人,早已看惯生死,这场小手术对他来说确实不值一提,像这样的情况也是少见多怪。
医生脱了防护服,白大褂很新。
他轻叹一口气,“那你跟我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