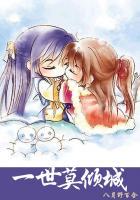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贤妇难为袁清免费阅读 > 第34章(第1页)
第34章(第1页)
大太太一听便火冒三丈:“这哪里是生了个儿子,分明就是生了个仇人。”又恨声道:“不必想,定是那何氏背后里挑三说四,那老四又向来同我不亲近,这就去告状了。可真真是白养了这个儿子了,倒同媳妇一个鼻孔出气,过来算计老娘。不行,我要去问问他,他可还记得是谁十月怀胎生下了他的,要去当官儿的人了,这般的不孝,可还有脸去教化乡民?”
周妈妈见着大太太是气得很了,忙拉了她道:“便是要算账,明儿个又再说。眼下老夫人等着呢,去得迟了,怕是要恼。”
大太太强忍住了满心口的恼火儿,等着到了妙心堂,立在门外长舒了一口气,这才命人去唤门。
进得屋里,便是满鼻子的藏香,大太太脸上挂着淡淡笑意,上前见过礼问道:“老夫人有什么吩咐,媳妇如今来了,只管说就是了。”
大太太心里已经想好了,若是老夫人发难,她立时便推到何氏身上去。一个小媳妇,进门不先夹着尾巴做人,倒是兴风作浪,每每都撺掇着老四过来忤逆她。
偏老夫人一个字儿都没提,只捂了胸口叹气道:“梦见了亲家母,心里跳得厉害。心想着约摸是亲家母想女儿了,这才叫了你来。你便支个小床睡在我旁边儿,若是亲家母又来,见着了你,想来也会高兴的。”
大太太一口气没上来,差点撅了过去。这是什么话,怎么就能说得出口来?可偏偏她又不敢反驳了去,老夫人这岁数,一个说不好恼了,气出个好歹,阖家上下都饶不过她。
无奈下,便吩咐了丫头支床收拾了铺盖。这般躺下,大太太瞪着黑洞洞的一片虚空,再闻着这满鼻子的藏香,只觉得心里烦躁的厉害,恨不得立时冲到棠梨阁将何氏骂个狗血淋头,才能解了这口闷气。
到了第二日,窦氏同邹氏一道去五福堂伺候,才知道大太太夜里被叫去了妙心堂,眼下正在老夫人跟前伺候早饭。
两人面面相觑,不知道这是闹得哪一出。又不敢掉头儿回了自己家去,唯恐大太太秋后算账。踟躇片刻,两人一道往妙心堂走去。好不好的,先打个照面再说。
大太太起得早,偏老夫人起得更早,夜里又没睡好,昏昏沉沉地在老夫人跟前伺候,老夫人瞧了一眼,便不高兴了。
朱老夫人是一辈子顺当的,活到这把岁数,撒个娇作上一回,也不嫌扎眼。将筷子一摔,捧了心口道:“多少年了,都没叫儿媳妇在跟前伺候,这么心血来潮一回,便要看儿媳妇的脸色。”又向着大太太哭道:“你一天挨着一天的,哪一日缺了儿媳妇伺候的。一个还嫌少,两个一左一右,你还只觉不满意,动辄便要教训了宏哥儿他娘,还有妙惜她娘,都生了孩子了,你时不时便要她跪在廊下做规矩。你当我死了,都看不见吗?眼下我不过使唤你一回,你便给我脸色瞧,老太爷还没死呢!”说着,就差人去叫老太爷来给她做主。
老夫人轻易不发火,这一发火,倒好似发了火灾,唬得大太太忙跪了下来,轻言细语地辩解道:“老夫人误会儿媳了,儿媳哪里敢给老夫人使脸色。原是儿媳有些择铺,换了地方就睡不踏实。脑子里轰隆隆的,脸上就瞧着不好看,并非是给老夫人使脸色。”
见老夫人还只捂着脸呜呜咽咽,大太太头疼不已,心说都半截身子埋到土里的人了,这般使性子,也不嫌难看!面儿上却忙堆满了笑,又道:“老夫人莫恼,要是想要儿媳过来伺候,儿媳真真儿是求之不得呢!这就搬过来,日日夜夜贴身伺候,老夫人瞧着可好?”
大太太这般说话也不过是为了哄一哄老夫人,谁家儿媳妇还能住在婆母的屋子里没日没夜的伺候,更何况他们这般的大户人家。岂料老夫人撩起帕子擦了一把眼泪,扭头却是应下了。还指了个丫头过去拾掇屋子,倒叫大太太脑子一蒙,当下就愣住了。
结结实实收拾了大太太一回,偏老夫人还不罢休,见着大太太愣住了,知道这话说得没诚意,不过是耍了嘴皮子哄她的,拉长脸又拍着桌子闹了起来。
朱老太爷便是这时候进了妙心堂,听见哭闹声,皱眉喝道:“大早上的,闹什么呢!”
大太太听见朱老太爷的声音双腿登时一软,朱老夫人却已经扶着丫头颤颤巍巍奔了出去,可把朱老太爷吓得不轻,忙上前扶住她道:“你这是做甚?当心摔了。”
朱老夫人捂着脸抽噎道:“都怪我为老不尊,就叫了大儿媳过来伺候我用早饭。以为自己是人家婆母呢,谁想人家就不乐意,就给甩了脸子。也是,四郎马上就要赴任了,人家是当官儿的娘,哪像我,两个儿子一个比一个不争气的。”
这话说得锥心,大太太从里头赶出来,忙跪在了廊下,哭道:“老太爷明鉴,儿媳半点这样的心思都没有,是老夫人误会了,真的是误会了。”
邹氏同窦氏先老太爷一步进了院里,还没说话,老太爷就来了。紧接着老夫人就哭闹了起来,这般看了一回,听了一回,眼下瞧着自家婆母跪在地上哭求,当时都唬住了,忙也跟着跪倒在地。
大太太余光里瞧见了窦氏和邹氏,心里恨得不行,此番在儿媳跟前可是丢了好大的脸了,又怨她们没事儿跑来妙心堂做甚,利刃一般的眼光瞪过去,邹氏当时便软在了地上。窦氏还好一些,忙扶住了邹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