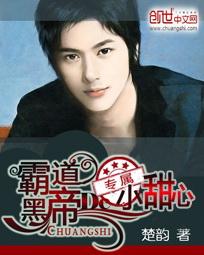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偏执沉迷学长 > 第88章(第1页)
第88章(第1页)
却没想到,真的会有人把他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认真又小心地记住。记了这么久,久到……那个听的人,早已忘记。
胸腔里像被柠檬水里涤荡了一遍,酸酸软软,又止不住冒出些温软的暖意,和——只承认一点点的难受。
洛橙不知道,当她无所谓地对他说出“能忘记的事情,能是什么重要的事情”时,他是用什么样的心情来回忆。
“老师,”鼻腔有些涩,洛橙笑说,“谢谢您。”
-
医院诊疗所。
“顾医生,”洛橙有些不解,“这两次治疗之后,我好像……能回忆起来的东西,越来越少。”
那个梦境里,似乎越来越多的,只是些重复的零散片段。
“就像长期使用消炎药的人,用药时间久了,也会产生耐药性。”顾泽笑着解释,“况且,人脑的自我保护机制,时常会下意识地替自己安排更合理、更利于自己的心理暗示。或许……你只是潜意识里,并不想记起某些东西。”
洛橙抿唇,看着顾泽:“还有别的办法吗?”
“如果你确定需要,”顾泽脸上,看不出太多情绪,“可以配合药物治疗。适量的阿米妥钠,可以帮助你更好地接受暗示。”
默了数秒,洛橙深呼吸了一口气,点头:“好。”
-
泽泰顶层的办公室,两个男人各有疲色地坐在沙发里。
“他们那些年操纵股价,利益输送的证据,已经交到季检长那儿了。”韩彻靠在沙发椅背里,松了口气似的说。
支着沙发扶手,简珩阖睫捏了捏鼻梁:“辛苦你了。”
这段时间,简泽恩用他手里剩下的那点股份,联合了几个先前同样被他“请”去养老的公司老人,着实兴风作浪一番。
“我每年那么多分红是白拿的吗?”韩彻轻嗤了下,又看着他摇了摇头,啧了几声,“你快别用那种感激的眼神看着我。我去,你不会是在小橙子那欲求不满,对我产生了点什么吧?别别别,我可遭不住。”
简珩好笑,又没眼看他,声音是疲累后的哑,低声笑骂:“闭嘴吧。”
韩彻忍不住叹了口气:“说真的,其实,我一直弄不明白,简瑜到底是怎么想的。能离开那个地方,有什么不好的?”
笑意收敛,简珩垂睫默然。
如果自我的意识,同父母家人的完全对立——如果能称之为家人的话,是选择痛苦地切割,还是与他们同化,享受赞美与便利?
简瑜自然是选择了后者的那个。而且自如又适应。
他不知道,如果他也是出生便在那个家里,或是……从没遇见过洛橙,会不会同简瑜一样。
沉默间,简珩的手机震动。是洛橙。
韩彻瞥见来电显示的“阿橙”,笑得一脸暧昧,扬眉指了指办公室的玻璃幕墙,示意自己先走了。
简珩无声笑着点头,拿过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