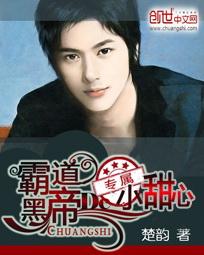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赖活着和死的区别 > 20 站在青春的暮年(第1页)
20 站在青春的暮年(第1页)
2016年,英国老牌重金属乐队“摩托头”的主唱兼贝斯手莱米·凯尔米斯特在当了数十年摇滚老混蛋之后,这位嗑药**以行事大胆不羁出名的老炮走了,享年70岁。在自传《whitelinefever》里有句名言:“人们不会因为死了就变得更好;这只是你们一厢情愿的想法。混蛋死了还是混蛋,只不过成了死掉的老混蛋!”
英国诗人布朗宁说:“四十岁是青春的暮年,五十岁是暮年的青春。”不知不觉中,自己在站在青春的暮年了。回望那逝去的青春,心情异常复杂。仿佛就在不经意之间,就走过了那么多的年头。按照我家乡古老的说法:三十不高是矮仔,四十不富是贫人。那么到了我们这样的年纪,基本上已经算是定型了。
我这里说自己站在青春的暮年,是按照自己还有暮年来计算的。想起过去的日子,真的就像一股云烟。在这40多岁的年头,自己有必要回首,总结一下自己所走过的道路,盘点自己的收获。正像我在前面说过的一样,一个人,在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上,其实上,他活到三岁,三十岁、一百岁,都是非常不容易的。而至于文字音韵学家钱玄同说的:人40岁就该死,不死也要枪毙。我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考虑。
40多岁过去了,我的事业没有成功——甚至什么是我的事业,我为之奋斗的事业是什么,还不明确。我就像一只长在荒野的动物,一直为生存而四处奔波着,至今仍没有一个稳定的单位,一份稳定的工作。对比起那些在年少时就发誓当科学家、当名人,至今已经功成名就的人来说,我的目标是非常不明确的。我曾经想过当一名作家,也曾经想过当一名官僚,但这些雄心壮志,都在生活的困苦中消磨得一干二净。
40多岁过去了,我的财富没有增长——甚至是减少,我居然没能存下来一分钱,反而是有一笔让自己每日耿耿于怀的债务。而且知道现在,我还是入不敷出。面对那些动不动就拿几十万、几百万年薪的人,不由得仰天长叹。远的不说,那些与自己年龄、学历、水平相当的人,由于有了好的机遇,也找到了舒适的工作,赢得了合理的收入。而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老化,那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又已经在收入上遥遥领先,使自己感到从所未有的郁闷。
40多岁过去了,我没能拥有健康。按理说,40多岁正是当年,是个上山可缚虎,下海可擒龙的年代,但自己却未老先衰,现在居然成了残疾人,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悲哀的事情了。看那些生龙活虎的年轻人,看那些身强力壮的中年人,看那些神采奕奕的老年人,自己直觉得就是废物一个,不说趁年轻时多赚钱,恐怕一不小心就成为家庭的拖累。一个穷人,如果连健康这一点资本都没有了,那确实是令人胆战心惊的。
40多岁过去了,我仍没有一个真正的家。家是什么?是一个房子下面养着一头猪。可是我的房子在哪里?我奋斗了几十年了,却没能赶上房价的变化,现在还是一个“房奴”。看着身边的那些人,住上楼房、别墅,并且把多余的钱,买了几套房放租,自己就觉得实在活得太窝囊。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国家正在宏观调控房价的疯长,但面对这天文数字一样的楼价,一声叹息。
够了!我不想再回首了!如此失败的人生,让自己越看越绝望。我不知道,随着儿女的长大,随着自己和长辈的变老,将是多么艰难的一个人生在等着自己。尽管如此,那些哲人驾驭我们,要想前看,要对前途充满信心,所以我也无数次幻想着自己的未来——但是,对于这样背景、这样生活处境的人,我还能希望会有什么奇迹出现呢?我会幻想突然康复吗?我会幻想明天有一纸任命书下来,叫我去当一任交通局长乎?我能幻想明天我买彩票,天降大奖,中了500万乎?我能幻想明天有一个富姐,扑进一脸麻子的我的怀抱,塞给我一千万乎?不!
这只是一个愿望,我不知能不能实现。2007年9月,我从武汉飞深圳,在空中,飞机遇到了气流,颠簸得很厉害,飞机忽上忽下,甚是怕人。因朱枸先生是第二次坐飞机,手心出汗,两脚发软,这时候思想就复杂起来:要是飞机就这样摔下去了,我该怎么办?然后我想得很多很多。诚然,自己从飞机上摔下,留给家人的将是无尽的悲痛。更为严重的是,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一旦塌下来了,将给一个家庭带来深重的灾难。
事后,跟一位与我一样苦难深重的朋友说起这事,他拍手大叫:从飞机摔下来?太好了!其实这样最好,像我们这种小人物,老是在生活中苦苦挣扎,就算挣扎到100岁,也不能给家里带来富足的生活,如果摔下去了,还能得到一笔赔偿款给家人,让他们过上稍微平静一点的生活。要是你生病了,不小心被人误杀了,那才麻烦,因为你得不到一分钱的补助,这才给家庭带来无穷的灾难。
确实,对比起那些大款、名人来说,无论怎么样的死法都是不值得的,因为有大坝的财富等着他们去享受。我一个朋友的母亲,今年62,生病住院,眼看就油尽灯灭了,但没有死,一直在昏迷之中,长达一年之久。所以,在这里,我授权买我的书的每一个读者,一旦我也出现这样的状况,昏迷不死超过48小时,你就有权利,或者说有责任用力掐住我的脖子,到我气绝为止,而你没有任何的责任。那时候尽管我可能没有知觉,我还是要从被你掐紧的喉咙里挤出一句:谢谢!
如果非要这样,请让我离去。
曾经,我们几个记者朋友聚在一起,说着说着,也说到“死”的这个话题来——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毫无顾忌地说起它,也许我们都在无望的生活中折磨得太深了,都深感绝望了。1994年5月,凯文·卡特,南非摄影记者,获得美国普利策优秀摄影奖,两个月后,他33岁自杀身亡:生活中痛苦太多,快乐太少。同学李某说,我希望我在70岁那年,被两个争风吃醋的女人在背后一枪打死。而一个花花公子说,我希望到我70岁那年的某一个晴朗的秋天,大喝一顿,然后找个性感女人一起风流,在**到来的时候,气绝身亡!问我如何?我说,顺其自然,一切由命,朱枸先生要是死了,那正是“九泉之下,才子又添一人”。众人抚掌大笑,将面前的啤酒一干而尽。
也许在这里我不应该谈太多生死的问题,这样的话题太沉重了,不符合本书的原则。何况,按照古老的说法,这也有点触晦头的忌讳,有些话弄不好真的会一语成孅。著名作家郑振铎一日跟朋友刘****闲谈,问刘****:“你晓得人怎样死法最痛快?”刘****无从置答。振铎说:“人最好从飞机上摔下来,死得最痛快。”不料,1958年10月17日,郑振铎领导中国文化代表团赴阿富汗访问,因飞机失事死,终年61岁。是不是有点恐怖?
展望自己的未来,我真的很迷惘。不过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活着就有希望。那真是一句废话一样的哲语,深含禅机,但又未必每个人都能参透它。朱枸先生“死”过一回后,却是感触甚深。尽管现在我现在没能看到一点希望,我还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时来运转,在厄运重重、连吃豆腐也崩掉大牙的时候,却发现崩掉我大牙的竟然是一块价值连城的宝石!明天没有发生,那我就等后天;40岁等不到,那我就等到50岁;50岁等不到,那我就等到60岁、70岁!《康熙王朝》里面的歌曲:“我真的还想再活100年”,那么我说,我真想活到100年!直到等到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