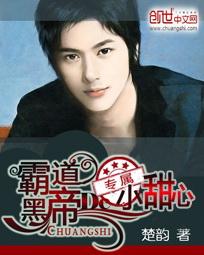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赖活着和死的区别 > 10 惶惶不可终日(第1页)
10 惶惶不可终日(第1页)
四年的大学时光转眼就过去了。到了大四下学期实习的时候,我们知道,大学生活已经是强弩之末了。但来不及留恋、伤感,就面临了毕业分配的问题。按照以往的惯例,我们毕业一般回到生源地,就是说,你从哪考上的,就回到那里。而畜牧专业的,基本上回到县畜牧,然后分到乡畜牧兽医站。不像现在的,你学兽医的,只要你有本事找到妇幼保健院接收,你就可以去;你学幼教的,只要有大学想要你,同样可以去当讲师。
更为主要的是,在我们专业每年都要分几个到农场,而且大多是劳改农场。按照当时的想法,这是最差的单位,所以大家都胆战心惊,生怕自己被发配(不是分配)出去。跟班主任、跟系主任说话都客气起来,成天把笑脸凑过去。现在看起来,我们的想法是多么的幼稚。后来我们班有两位仁兄“不幸”成行,其中一位一生气连毕业照也不照了。可是前两年我见到他们的时候,觉得他们过得比任何一个同学都好。而我们班分配回去的,有些现在还在兽医站呆着,有的分到饲料公司早就下岗了,有的转行做着跟专业毫不沾边的工作,而一位杨同学,在一个几千人的农场里当领导,据说,美国就考察了好多次。另一位分到劳改农场的,穿上警服,现在的警衔都是一督了,同学聚会的时候,都感慨万千。
我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我回到生源地后,就跟女朋友相隔万水千山了。但我又没有这个能力去到她工作的地方去工作——那已经是跨地区了。我出动所有的关系,终因没有关系,最终断绝了这个念头。有本事的同学有的在南宁找了单位,有的进了地区、起码是县的单位,我还是毫无着落。毕业前,我在我县的一个鸡场实习,在那段时间,我托朋友们帮我找关系,甚至《广西文学》的编辑梁宪华先生也帮我找人推荐,想留在县城,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帮上忙。
我不喜欢干畜牧兽医这种工作,我觉得自己学业不精,很难胜任这些具体的技术工作。确实,在大四的时候,多是专业课,我都没有认真去学。比如给鸡、猪、牛人工受精,比如给猪、马、牛、羊接生,给初生的小猪剪獠牙,给奶牛挤奶,制作香肠和酸奶,为一个猪舍画设计图等等,我都不会。而说到最专业的东西,阉鸡、阉猪,不知从何下手,有一次实习,我大着胆扎下去,鸡卵没有找到,却把鸡肺捅着了,那只可怜的小公鸡,挣扎着在我的手中死去。而我们班上一些同学已经在星期天到外面摆摊,帮附近的农户阉鸡挣钱了。就连最基本的打针也不熟练。我在南宁兽医站实习的时候,有一天我值班,有建筑公司打电话说他们饭堂养的几十头猪不吃东西了,要我们马上派人过去。当时站里的人都出诊去了,只剩我和一个老乡、同学陈凯,这家伙的学业比我还差。于是我们硬着头皮带上药箱出发,天气很冷,那个建筑公司在一个很远的地方,我们到了那里以后,根据自己半桶水的知识,初步断定是感冒了——那时候天很冷。于是,我们给它们打针——打飞针。但是,要给这一群30多头猪打针,真是难为了我们,往往是不知哪个打了,哪个没打过;哪个打着了,哪个没有打进去。整个猪圈被我们搞得猪嘶人叫。半个钟头后,人也累了,猪也累了,我们决定鸣金手兵。公司的人对我们非常感激,留我们吃饭,煎了四五十个鸡蛋给我们——鸡蛋能吃多少啊?我们放开肚皮直吃,才消灭不到四分之一,以至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一见到煎蛋就反胃。回来后,我整晚都睡不着,生怕把人家的猪治死了。第二天,我们忐忑不安地打电话去问情况,那边说,好了,已经吃东西了!这让我们非常惊奇,后来我们的老师劳教授说,你们是歪打正着,那些猪,你们就是不给它们打针,但那么拼命地赶,他们得到了剧烈的运动,也就好了!
那时候,农学院的牛胚胎技术是在全世界都有名的,所以,我们也要学一点。给鸡、猪、牛人工采受精,给猪、马、牛、羊接生,给初生的小猪剪獠牙,给奶牛挤奶,制作香肠和酸奶,为一个猪舍画设计图、种牧草等等,尽管是一知半解,但我想我该毕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