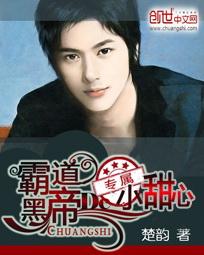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伴星引力有肉吗 > 第44页(第1页)
第44页(第1页)
我拿过一只圆珠笔,用牙咬下笔盖,伏在收银台前书写。他想要偷看,立马就被我发现。
“真不能看啊?”
“再看我就不写了。”我将手盖在明信片上。
他撇撇嘴,像个小孩一样做出不满的表情,然后将背转过去,走到货架旁去看微缩版的协和礼拜堂模型。
我迅速写完明信片,填上兄弟们和妈妈的地址,最后一张上面我写了池易暄的宿舍地址。
不幸的是,被我寄出的那一批明信片丢件率高达50,其中就包括寄给他的那张。这可能是上天给我的暗示:我无法到达有他在的彼岸。
眼看着天边泛起鱼肚白,池易暄的房间里终于有了动静,他出了卧室径直去卫生间洗漱,然后从冰箱里拿了个面包叼在嘴里,低头系起领带。
我看着他脚步匆匆,系完领带穿上西装外套,借鞋柜之上的镜面抓了下头发,出门之前都没有给我一个正眼。
如果他刚才骂我两句,这事或许还有余地。
我慢吞吞地从沙发上爬起身,摸到行李箱边,将带来的衣服一件件塞进去。我没心情叠,哪儿缝隙多就往哪儿使劲锤。
明明来的时候一个箱子够用,现在东西却塞不进去了。我将行李全部倒在地板上,打算把不要的杂物扔了,两盒写着英文的止疼消炎药忽然从里面滚了出来。
我的伤已经好了,不再需要这些。我将它们捡起来扔进厨房垃圾桶,回到行李箱边继续整理被子,却还是塞不进去。
我一阵胸闷,去阳台上透气,半天不见好,余光瞥见阳台一角摆着一只陶瓷烟灰缸,橙色的烟头断了半截,皱在一块。我走到烟灰缸旁,从中捻起一只还剩半截的香烟,两块灰色的烟灰从指间簌簌往下落。
阳台边沿摆着一只红色的塑料打火机,池易暄经常在这里抽烟,我学着他的模样靠上扶栏,身体前倾,探进从钢铁森林间穿过的风里,点燃那只香烟。
含上他咬过的烟嘴,有种占到他便宜的错觉。马上就要无家可归了,居然还能在这个关头想这种事。我可能真有点毛病。深吸一口烟后,当即呛得咳了好几口。
这是我第一次抽烟。以前总看到年长的男人们靠抽烟来放空脑袋,可我脑袋中的思绪却缠结到了一块。我想不明白池易暄为什么会喜欢抽烟。
我摁灭烟头,又鬼使神差折返回厨房,从垃圾桶里翻出药盒。
我舍不得扔。这是我哥暗中托韩晓昀带给我的。
不知道池易暄知道我受伤时,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情。韩晓昀八成说我是英雄救美受了伤,他肯定在心里骂我没事找事,出门前在家里翻箱倒柜拿出止疼药和消炎药赶了过来。
医生给病人看完病了都会开药。他不是没有去过医院的人,这种事怎么会不知道?
要么是太过心急来不及细想,要么就是想要亲自看我一眼。
我想象不出来,当我坐在医院门前的台阶上等出租车时,他到底躲在哪个我看不到的角落里抽烟。
他是在乎我的。
我摸出手机,点开通讯录。
犹豫许久,还是拨通号码,将听筒贴到耳边。
哥,我们都诚实一点吧,我不想玩这些口是心非的游戏。
“嘟嘟”的电子音仅持续了五秒钟,便被他挂断。第二通电话打过去,提示音变成了“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
他不是轻易改变想法的人。我一阵心慌,奔到玄关,踩着鞋跟就跑出了公寓,冲到停车场出口处寻找起他的身影,好一阵后才意识到他早开走了,我真傻。转身朝马路边跑,想要叫一辆出租车,期间却被鞋带绊倒,手里的东西摔了出去,骨碌碌地滚。
抬眼一看,才发现我居然一直攥着他给我的药盒。
这一摔,浑身的骨头与水泥地热烈地亲吻,眼前冒起星星,我才想明白。
我想要向他道歉,为我以前做过的所有错事。为我的愚钝,我的卑劣。
我以为偷走白炀,便能够拥有他的一部分。
我希望我们还能在雨天里踩水,在篝火旁将棉花糖外皮烤得酥脆。他开车载我,我拿着地图指路。我想和他拥有更多美好的记忆,我希望那些记忆对他来说也是锦上添花。
以后无论是白炀还是黑炀、cdy还是sandy,我都不会再犯浑。
哥,原谅我吧,我想要被你管。
黄色出租车从公寓小区一路开到池易暄的公司楼下,一路上我酝酿了许多话,眼眶都要融化,可站到直插云霄的高楼面前,却又抬不起腿。
第一次来时是盛夏,我想要留下,他让我滚蛋。现在又是如此。人生可能就是由重复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