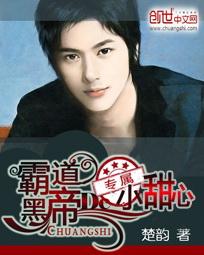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主角带着手机重生 > 第69章 年12月10日 超量午餐(第1页)
第69章 年12月10日 超量午餐(第1页)
下课铃声一响,熊孩子们欢呼着要出去玩雪,一窝蜂地聚教室后穿外套。附小没有储物柜,学生们冬天的外套都搭在椅背上,严维头疼于总有学生跟他告状:“老师,他又把我的衣服踢脏了”;或是有的学生衣服总掉地上,一节课四十分钟要捡上十八回,干脆弄了两个可折叠的落地晾衣架,给泼猴们挂外套用。
严维下了课也没走,在给季疏缈前面的同学讲题。
“缈缈老大,倾倾,出去玩雪啊!”有女同学叫道。
季疏缈一点兴趣都没有,懒懒地往课桌上一趴:“不去。”
刘倾倾只觉得她可爱的很,笑着和那女生说:“我也不去。”
“这么冷,你别叫倾倾。”一个女孩说着,把邀请她们的女孩拉走了。
季疏缈疑惑:“为什么天冷不叫你?”
刘倾倾扬了扬自己一双手,答案显而易见。
“哦。”季疏缈重新趴了回去,看到她椅背后的外套皱眉,“你的外套这么薄?”
“还好。”刘倾倾把外套伸出来的袖子往里藏了藏。
她越藏季疏缈越觉得不对劲,伸手拿过她的衣服,一瞬间愤怒充满了胸膛:“他们连一件厚衣服都不给你?”
手里的这件老旧的黑色外套并不是羽绒服,拿在手里轻飘飘一点重量都没有,里外都是透风的布料,里面填充的棉花已经起块结团。
季疏缈因为盛怒而红了眼,刘倾倾又何尝不是,垂下通红的眼,说不出一个辩驳的字。
贫穷和不被爱,都是不可触及的隐私。
“季疏缈,跟我出来。”严维不悦地叫道,说完先出了教室。
季疏缈压下情绪,跟在他身后。
严维叹气:“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但最好别做。”
季疏缈问:“为什么?”
“去年,我和几个老师凑钱给倾倾买了一件羽绒服,她当天就挨了一顿打,被她爸妈脱了衣服打得皮开肉绽。我去家访,她爸妈就当着我的面骂,说她贪慕虚荣,偷拿家里的钱买衣裳,打扮得花枝招展勾引人。”
他们是在打严维的脸,嫌他们老师多管闲事。
季疏缈气得掉眼泪:“怎么会有这种人啊……”
严维止不住叹气:“天底下什么样的人没有啊。总之你别给她衣服,去年冬天因为衣服的事,她天天挨打。”
季疏缈虽忿忿不平,到底在严维的注视下点了点头。
中午放学,刘倾倾依然要回去,穿上那件破棉袄和季疏缈说再见,季疏缈不高兴地撇着嘴,拉着不让她走。
刘倾倾哄她:“我回去晚了要挨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