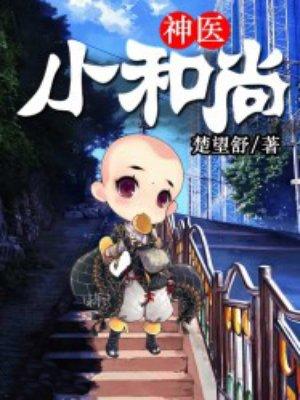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王子的游戏漫画 > 第41章 前后(第1页)
第41章 前后(第1页)
在听闻医生建议自己应做一个堕落女士,且需要绝对稳定的那一刻,艾尔娜下定决心。与其以字里行间的真相给奶奶带来别样冲击,倒不如暂且停留在被都市放荡所染、不懂事的孙女这一误会中。
艾尔娜长长地叹口气,疲惫的身躯倚在窗框上。
赶到医院看到昏迷不醒的奶奶,艾尔娜一时无法正常呼吸。发现爷爷倒地那日的记忆骤然袭来,仿若被扼住咽喉。
爷爷倒在书房地板上,奄奄一息。第一个发现的是前去通知喝茶时间的艾尔娜。死因是心脏麻痹。奶奶晕倒亦是因心脏不适。
若不是发生在人多的城中。若再晚点到医院就糟了。倘若奶奶的心脏再弱一些。万一奶奶也如爷爷那般,突然某天,连一句道别都未说便离去。
仅是这般,泪水瞬间涌出。果真如此,艾尔娜此生都不会原谅自己。
热爱命运。
艾尔娜忆起支撑自己至今生活的那份信念,用力按压住滚烫的眼眶。不愿陷入自怜。越是此般时刻,越要坚强。
首先,集中精力让奶奶恢复健康。待其恢复至可长途跋涉时,一同回到伯福德即可。而后用答应向帕维尔借的钱租房子,将这座城市彻底遗忘,在那里开启新生活……
“绝对稳定。”
闪现的医生建议,斩断了艾尔娜拼命想起的希望。
失去承载一生回忆的珍贵豪宅,于辗转租房的生活中,绝对的安定还能存在吗?
艾尔娜望着窗户中自己的脸,眼神再度迷茫。
这定会给奶奶带来极大混乱。但又有何办法?当下已无法守护乡下的房子。
若如此,是否应接受托马斯·巴登的求婚?
一想到或许那条路最为简单,自己便觉无比卑微与悲惨。竭尽全力的努力竟不如死心的结果。虽不愿承认,但摆在艾尔娜眼前的现实分明如此。
如石像般呆呆守在原地的艾尔娜,直至傍晚才离开窗前。病房前原本访客众多、人头攒动的走廊,此刻已变得冷清。
艾尔娜坐在走廊最角落的长椅上补妆。不论如何努力,都不及丽莎做得好。越努力越糟糕,恰如眼前的现实。
缓缓缓过神的艾尔娜,抑制住想要卸掉这糟糕妆容的冲动,从座位上站起。傍晚的长影落在她迈向病房那沉重的步伐之后。
打开病房门前,艾尔娜如戴上面具般,面带微笑。
即便被沉重而艰难的现实压得喘不过气,仍要热爱这生活。因这般的自己而害羞伤心,艾尔娜的笑容愈发灿烂。
艾尔娜。艾尔娜。艾尔娜。
虽高潮已过的夏日即将结束,但这个名字依旧热度不减。处处皆是。咬住这女人不放,近乎成为一种疯狂的游戏。
比约恩缓缓睁开双眼,仿佛抹去那如耳鸣般萦绕的名字。如今已至尾声的牌局,热度渐消。转眼间已至天亮,情有可原。
比约恩托着下巴坐在桌前,呆呆望着窗帘缝隙间透进的一缕晨光所投下的细细光线。艾尔娜。就在她的名字再度浮现在意识中时,服务员进来了,这几日她的名字想必自己听闻甚多。他放下茶杯,又如来时般悄然离去。
比约恩放下轻抚泛红眼角的手,握住那杯子。饮下一杯泡得发涩的茶,昏沉的头脑方才清醒。艾尔娜。那女人的名字也随之清晰起来。
听闻她仍在医院照料奶奶。
若顾及他的颜面,他亦会佯装相助,可哈尔迪子爵似乎已自暴自弃,彻底回避了巴登男爵夫人。支付医药费的是帕维洛尔,那女人与那试图夜间出逃的画家。
在玩闹呢。
忆起那一本正经解释说是家人般朋友的女人,比约恩笑了笑。
极大可能,钱不会说谎。这世上没有为无心女人花钱的糊涂小子。
不论是朋友、家人,还是恋人。比约恩不想再管他们究竟是何关系。打算将那最为急需的钱交予那陷入困境的女人,而后结束这场游戏。若不是父亲那荒唐的命令与最糟的丑闻,他早就如此行事了。
轮到自己了,比约恩淡然放下结束游戏的牌。已然自暴自弃的他们乖乖接受了失败。
胜利了。
比约恩一口气抹去这未带来多少乐趣的事实,深深地倚在椅上,闭上双眼。离开纸牌室的喧闹声停止后,清晨特有的清澈寂静将他笼罩。
“嘿,比约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