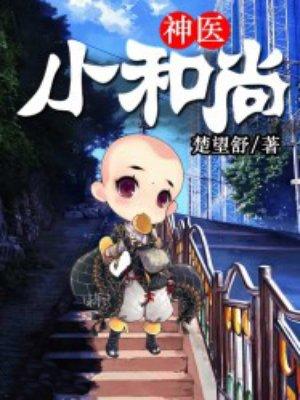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千岁宝掌和尚 > 40 惊醒(第2页)
40 惊醒(第2页)
惶惶十八年,祸星二字重若千斤,早早便压弯他的脊梁,磨平他的脾气,使他夜不能寐,愧疚难当。
曾几何时,他总觉得是自己害死了邵毅轩,也是自己害长澹边境生灵涂炭,结果现在居然有人告诉他——其实他原本可以不做这个祸星。
那……那如此一来,他之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活过的十八年,到底算什么?
窗外寒风刺骨,玄鹄担惊受怕地守了李熙大半夜,却也无法将他从梦魇中唤醒。
其实李熙也知道玄鹄在喊他,可是醒不来。
一片黑暗中,李熙只能满身冷汗地在噩梦里挣扎,奔跑,却撞不开面前锁住他的牢笼。
李熙感觉自己的手腕脚腕都绕着线,傀线。
李熙想剪断这些线,想为舅舅报仇,为母亲报仇,想从此彻底摘掉这顶祸星的破帽子,更想离开京都,可当他一旦有了这念头,这些傀线便在他身上缠得更密更紧,让他无从下手。
很乱。
乱如麻。
而他自始至终都卑如蝼蚁,从前是,现在也是。这种仿佛与生俱来,理所当然的卑微让他白白顶着这么个贵姓,却要受阉人要挟,兄弟迫害。
不甘心啊,人活在世上,难道只要全须全尾地活下去,便足够了么?只是活着便够了么……?
……难道如现在这般委曲求全,糊里糊涂的活着,连自己的前路生死都不能掌握在自己手中,便够了么?
几乎是在一瞬间,先前在脑子里闪过的那点模糊念头,忽然变得无比清晰,而李熙也叫这念头搅得胸口憋闷,头痛欲裂,已经有些喘不上气。
关键时刻,还是玄鹄急中生智,不顾李熙在烧,直接拿一盆冷水浇醒了他。
冷水浇下去之际,风停,李熙骤然睁眼,一双眼睛亮得渗人。
玄鹄被李熙这模样吓了一跳,有心要问李熙在裴怀恩那里见着了什么,却见李熙对他眨了眨眼,在从噩梦中清醒后不久,便当先神色古怪地问他:
李熙问他,说:“玄鹄,你见过骨鱼摆尾么?我觉得我现在就好像那条鱼。”
顿了顿,再冷冰冰地阖眼。
外头的风又刮起来,玄鹄茫然地俯身,听见李熙正在那自顾自地喃喃低语。
“……我不想再做鱼了。”
玄鹄听见李熙说:“舅舅,母妃,求你们保佑我,我已经……不想再做这样可怜的一条鱼了,总有一天,我要做鱼钩,做渔翁,做餐桌上的食鱼人。”
-
裴怀恩将李熙表面上那点软和当了真,拿吓唬小孩的法子去吓他,未料适得其反,倒让李熙自此生出反抗之心,不愿再为他所用。
可惜裴怀恩不会读心,猜不到李熙心里一时一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