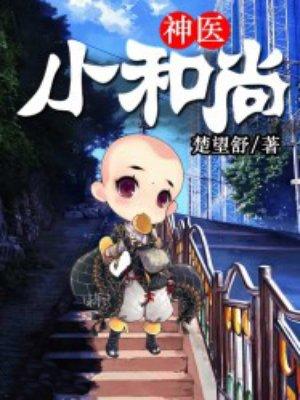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猫咪森林无限金币版 > 第42章(第1页)
第42章(第1页)
我笑起来,“小猫,你真的觉得他们需要我们原谅?不不,我不这样认为。”
她有些沮丧,“你说的对,他们才不在乎,是我们太天真。”
我满不在乎地摇摇头,“所以做人不要太执着,这样对大家都好,不会感觉那么辛苦。”
她忽然奇怪地看住我,“泱泱?”
“嗯。”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说话的口气活像一个人?”
“噢?”
“杨萧也常常对我说,做人不要太执着。”
“哦。”
“可是,如果把一切都看作尘埃,人生会不会变得很乏味也很没意义?我也不知道自己为甚么就是放不下,但是如果真的可以轻易放下,我就不再是我,是甲乙丙丁任何一个,就是不是林小猫……唉,我在讲甚么啊?”
其实我明白她的意思。
是啊,每个人既平凡又独特,因为生活在其性格和内心深处打下的烙印,有些浅淡,有些峥嵘,有人善于隐藏,有人拙于掩饰,因此一个人是一个人,正如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
现在,我口吻轻忽地告诉林小猫――做人不要太执着。
可是,她不知道我心口的挣扎与疼痛,不,她不知道,他们都不知道。
这么多年来,一直是我一个人承担一切。
一切失望与心碎。
于是我愈发努力营造一个坚硬的外壳,我不要别人看见我脆弱的内在。
那只会让我更加沦为一个笑话。
尽管我在心里大声嘲笑着自己,嘲笑那些继承自爹爹和妈妈,一样懦弱而又可笑的骄傲,但仅只于此。
因为这些都是我自己的事,必须独力承担,独自忍耐。
这几个月我见钟律师的次数超过他担任监护人后我们见面次数总和的数倍,在接受治疗期间也因为他的坚持曾经在钟府小住一段时日,钟伯母忙前忙后亲自照顾我,丝毫不介怀我过去的刁钻任性。
我看着钟家父慈母祥天伦共叙的样子,心里非常惆怅。
钟律师一直没有提起母亲,仿佛根本没想过应该将我生病的事知会一下对方的直系亲属。
我也就绝口不提。
真是奇突有趣的默契。
倒是钟伯母,有时候会局促不安地微笑着安慰我,“泱泱,放宽心,耳朵一定会好起来的,呃,都会好起来的。”
我伸手握一握这位善良女性的温暖手掌,嘴角抿出一个向上的弧度。
你们对我的好我都知道,都知道呵。谢谢。
妈妈,你现在过得可愉快?有个爱你的先生应该会感觉幸福吧?是否偶尔还会想起爹爹,和我?在你的记忆中,我们的存在只意味着背叛和寂寞吗?那么请你忘记吧――你已经忘记我了,是么?
所以,我情愿一直这样下去,所有人都保持善意的沉默和回避,留下想象的空间。
因为,留白总是胜过决裂。
可是妈妈,为甚么,你连这样都做不到?
周末,钟律师约我一起晚餐。
菜色精美,茶点可口,灯光桌布和餐具也都布置得恰恰好,整个晚餐过程轻松而愉快,我很配合地听钟律师谈起事务所接到的有趣案例,或者由衷赞美钟伯母亲手烤制的葡式蛋塔何其美味,偶尔也在长辈满是笑意的注视下和钟诺言口角往来针锋相对……
可是不对。
虽然说不出究竟,我还是分明感觉到了甚么。
夜渐深,墙边的落地古典红木大钟的指针早已过了九点,我两次想要提出告辞,却都被钟律师挡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