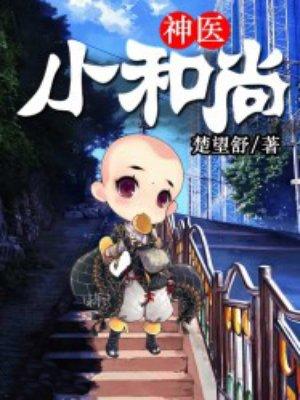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猫咪森林汉化版 > 第38章(第1页)
第38章(第1页)
“泱泱,”钟诺言过来扯我的胳膊,“雨太大,明天再来找……”
“走开。”我甩开他的手,头也不回,固执地伏在地上拨开乱七八糟的树枝和草叶。
“周泱泱,”他一把掰过我的肩头,“它不在这里!”
“走开!”我推开他。不,他根本不知道我在找甚么。
“周泱泱!”他生气,大力将我拽起,指掌如铁钳任人挣扎都无法抽身。
“放手!”我暴怒,抬脚就踢,“钟诺言你放手!”
“你还不明白吗?周泱泱,”他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你要找的东西根本不在这里!”
我愤怒地瞪他,他也不甘示弱回瞪过来。
心口有甚么沉重的东西开始瓦解崩溃,我但觉气苦,眼眶发热,喉咙口如梗巨石,要拼命抑制才能不让眼泪流出来。
“你不明白,”我哑着嗓子一字一字说,“你甚么都不知道!”
“我明白,唉,我知道……”钟诺言的声音却变得温柔。
手臂上的力道突然消失,未及反应,一双有力臂弯揽过来,将我圈入一个温热宽厚的胸膛。
“泱泱,你需要的是很多很多爱,和很多很多的温暖,在这里你找不到,明白吗?”
“想哭就哭啊,不需要忍得这么辛苦,嗯?”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努力装出强悍并叛逆的模样,心里堆积了太多的不快乐,那许多许多的渴望和失望和渐渐沉淀的绝望都令我无法自抑想尽情宣泄,可是我不能,也不愿意――我不要别人看到我内心的软弱和惊惶。
无论如何抗拒长大,成长依旧不可避免。
幼时就学会克制眼泪,等长大才发觉成年之后想要放声痛哭变得愈加困难。
我不记得自己有多久没有真正哭过――十年?也许更久。
而现在,在这泠泠冬雨中,钟诺言的怀抱稳定可靠。
我听见宛如受伤的小动物般抽泣哽咽声,半晌才领悟原来那是我自己在哀哀哭泣。
眼前有太多的场景飞掠而过,这些那些的记忆碎片,锋锐如刀,一刀刀都割在心头。
“没人需要我,没人爱我,他们都选择离开,没人愿意带我回家。没有人。”
“嘘,我知道。我都知道。”
我终于痛哭出声。
正自哭得痛快,身体一凉,钟诺言伸手将我扶直。
“每次痛哭五分钟足矣,你已经哭了至少十分钟,再不克制恐怕要引起误会。”隔着雨水和泪水,也依稀可以看见他嘴角的似笑非笑。
我自觉脸孔开始发烫,眼角偷偷一瞄,果然,不远处的操场入口已经有人过来探头张望。
他回身去跑道找到我的外套和背包递过来,“跟我去取车。”
我被他适才的话噎得没好气,“不要,我要找小猫。”
“喂,周泱泱,你是自己跟着来?还是要我抱你走?”他笑嘻嘻踏前一步。
我吓一跳,急急后退一步,没奈何只得点头,跟着他离开了操场。
其时恰逢大礼堂演出结束散场,许多走读生和校外人员沿着学校林荫道往大门口走,大多有备而来手里打着伞,我们两个被雨水浇得透湿从校门附近的操场入口出来,举止狼狈,引来诸多注目礼。
钟诺言居然施施然不以为意,一路上遇到熟人招呼也一一微笑应对。
就算我平日举止再张狂不经也无法继续泰然自若,低下头加快脚步往系教学楼方向走去,到最后几乎已是拔腿飞奔。
“嗨嗨,到了,就是这边。”钟诺言大踏步赶上来捉住我,眼睛略略眯起,笑了。
我才要说话,鼻子发痒,一口气打了三个喷嚏,索性闭上嘴,板着脸孔上了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