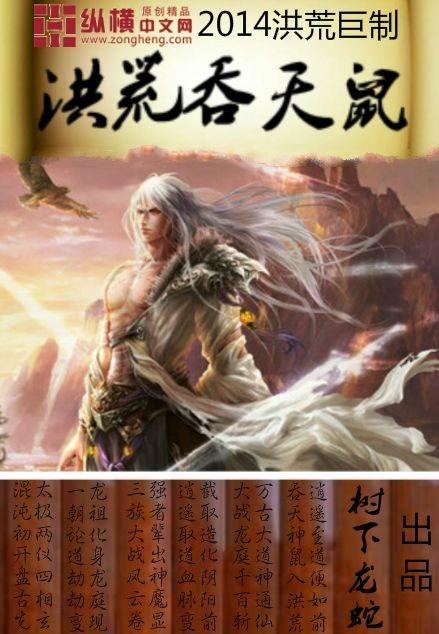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资本剑客 百度 > 第23页(第1页)
第23页(第1页)
他说完这句话,带上自己的文件夹转身出去了,整个会议室里的人都在注视着他的背影,很多眼力好的,感觉他们老大罩在身上的那件外套好像松了一点似的。刚刚晋升为财务总监的房宵没有高兴——因为他知道,无论他叫总监,还是叫主管,或者什么都不叫,这些在短时间之内都不影响他的收入水平,他忽然用笔头戳了戳旁边的赵轩,小声问:“哎,老大受什么刺激了?”赵轩回了他一个蛋疼的表情,拎起外套走了出去:“周末不休,大概今天晚上不用加班了,大家早点散吧,最近都辛苦了,回头我请你助理吃顿饭。”房宵愣了一秒钟,反应过来瞪大了眼睛:“我擦,我助理跟你丫有什么关系?”赵轩对他露出一个“风情万种”的笑容,拎起外套转身走了。李伯庸突然感觉到有种紧迫感,尽管以他的年龄来说,他已经算是很成功了,可是还不够,他想……还不够。他就像是一株迫切想要长得顶天立地的树,外面的世界那么大,而他立足的地方这么小。他曾经沾沾自喜,因为自己只是一个农村长大的穷小子,到最后却比那些城里年轻人活得都好,有房有车没贷款,有自己的事业,虽然还没有老婆……不过也只是暂时的。而现在,他突然发现时间不够了,比如无论他获得多么大的成功,走过多远多了不起的路,世界上只有两个人,他最想让他们知道,而现在,这两个人中间,有一个已经不在了……在他还在自己的路上磨蹭的时候。他永远也不能逢年过节的时候,在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和那个什么都没见过的傻老太太显摆,自己做了什么什么了不起的事,上了什么电视,上了什么报纸,赚了多少钱,卖了什么东西,下次回去可以给她买什么高级的东西。现在只剩下傻老头一个人了——李伯庸感觉自己变成了一只惊弓之鸟。他关上办公室的门,一屁股坐了下去,桌子上乱七八糟的,烟灰缸就像个小小万人坑一样,罗列着码得高又高的死而不安的烟蒂。李伯庸叹了口气,靠在椅子背上,仰面朝天,觉得脑子有点缺氧,感觉很不好。当一个人诸事顺利,认为一切都还不错,虽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成就,但是也没什么特别大的篓子,一切都在往好的地方发展的时候,他会比较有空,也比较有心情。这种时候,人一般看起来会比较自信,也会非常乐意和别人分享自己的经验。他通常会劝别人站得更高一点,看得更远一点——好像他自己的心胸有多宽阔似的。而有的时候,这种装逼用的心胸其实不能持续很长的时间,因为再牛逼的人也会遇到逆境,也会手忙脚乱,按下葫芦浮起瓢,也会焦虑。人一旦因为某种原因开始焦虑,心胸就宽不了了。这个逻辑非常容易理解,因为他的注意力因为焦虑而被高度集中在了一件或者几件事上,分不出精力和时间去站在宇宙的制高点上指点江山了。也就是……俗称的“想不开”。比如李伯庸,他现在就想不开了。这种感觉非常的难过,因为生理上的疲惫通常会引起心理上的抑郁,抑郁的时候总是会想起很多不好的事,发生很多无中生有的担心,或者产生某种因为不自信而引起的过度自我膨胀。李伯庸脑子里一片空白地坐在那里片刻,忽然想起麻烦了杨玄那么长时间,还没有感谢过人家,于是给她打了个电话,可是电话响了十几声,直到自动挂断了,也没人接,李伯庸愣了愣,一连打了三个电话,都没有回复。他慢慢地皱起眉来,开始觉得有些不对了。杨玄那天醒来的时候其实是尴尬了一刹那的——其实谁睡得像个死猪一样,一不小心滚到了别人身上,还把别人压得半身不遂……都会尴尬一刹那的。尤其半身不遂的那个还好像占了多大便宜一样,脸都红到了耳根上,结结巴巴地把屎盆子全扣在了赵轩头上,硬说是因为他开车不稳。那以后小一个月的时间,李伯庸都没有出现在她面前过,只是每天晨昏定省的几条短信,看得出李伯庸不大会发短信,标点符号一律没有,一开始非常考验了一下杨玄的断字水平,后来大约是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开始用空格代替逗号。偶尔会有一些暧昧短信,不过李伯庸不是赵轩,非常适可而止,绝对把这个度控制在进退得当、大家都能一笑而过的水平上。这时候,杨玄就发现李伯庸这个人身上,有种生意人特有的圆滑——然而这一点点的圆滑,也很难改变他在她心里那个根深蒂固的二货形象。她依然是每天玩一样地上班带队,平平淡淡,了无起伏,少有艳遇。偶尔穆晓兰被赵轩骚扰得不胜其烦,可能会找她支个招。直到这一天下班,杨玄插上耳机,把脑袋塞在大衣连的帽子里,脖子上还围了一条围巾,盖到了鼻尖以上,只露出一双眼睛。闹闹在她大得过分的兜里,露出个毛茸茸的脑袋,正非常新奇地以全新的视角观察着下班高峰时候愚蠢人类的生活。杨玄刚刚和周姐申请了,以后闹闹不再轮班,专门归她一个人养了,白天来办公室的时候可以把闹闹也一起带过来,办公室里依然有它的小屋——这充分说明了大家对玩猫的兴趣都很大,养猫就算了。就在她以这样一个回头率百分之百的非主流造型,一路被众人围观到了地铁站的时候,一辆停在那里的宾利里突然露出一个人头,那个人盯着她看了半天,好像有点难以确定似的,直到她走到地铁口,感受到里面冒出来的热气,略微把围巾往下挪动了一点的时候,车里的人才叫出了她的名字:“杨玄!”康金凯突然在闹市区听见陌生的声音叫自己的名字,杨玄以为自己听错了,而对方突然在闹市区,看见一个裹得像个华裔木乃伊一样的女人,兜里还装着一只不应景的猫,也非常有同感地认为自己是看错了。直到杨玄回过头来,围巾掉在了脖子上,露出一张捂得微微有些发白的脸,他才呆了片刻,回过神来,心里忽然有种异常幻灭的感觉。杨玄感觉这个人有点眼熟——她有一点细微的脸盲症,以前工作的时候会很努力地记人,甚至有一份秘密资料,里面写着每个人的名字,以及他们长相的特征——比如谁谁有张鞋拔子脸,谁谁脑袋上长了一块斑秃,目测形状接近红海……之类。现在没有这个必要,于是这个好不容易练出来有点成效的神功,慢慢地又退化回去了。她又恢复到了那种看谁都眼熟,看谁都想不起来是谁的状态里。看了半天,只得出了这男的……有点骚包这个结论。男人关上车门,对她笑了笑:“晚上有时间么?可以找个地方聊聊么?”杨玄眨眨眼睛,男人脸上并没有露出一点尴尬:“不记得我了么?我是康金凯。”杨玄终于皱了皱眉,这个细微的表情使得她脸上的一点迷茫神色褪尽了,异常柔和的眉眼显得有些凌厉了起来:“是你?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康金凯背对着车,对她做了一个邀请的动作:“上车来我们可以详细谈谈。”杨玄往后退了一步,目光在他脸上扫了一圈,把正在往外钻的闹闹的脑袋按回了兜里,脸上露出一个有些冰冷的笑容:“对不住,咱俩有那么熟么?我还真没觉得有什么好和你聊的。”她说完,冷淡地点了点头,拎起围巾的一角,重新遮到自己的鼻子上面,转身就要走。康金凯的目光闪了闪,突然在她身后说:“你知道王淑么?她最近嫁给了陆朝阳,她妈吕安安联合了陆家,正在想办法活动,要把王洪生从监狱里弄出来。”杨玄的手指还没来得及从围巾上拿下来,脚步就倏地顿住。康金凯双手抱在胸前,好整以暇地看着她:“现在我们有话题了么?”杨玄犹豫了一会,她的手指尖在户州的深秋里冻得通红,停在米色的围巾上,仿佛有了那么点十指如蔻丹的感觉。然后她默不作声地转过身向停在那里的车走过去,康金凯脸上露出一个胜利的笑容,侧过身去,帮她拉开车门。这个男人严格来说长得算是英俊,只有笑起来的时候,本来就极薄的嘴唇抿起来像是一条线一样,在他的脸上划过,怎么都有点皮笑肉不笑的感觉。车里已经有人了,除了康金凯之外,还有两个五大三粗的男人,一个是司机,一个坐在后座上,都是一身黑,大白天还戴着墨镜,唯恐别人不知道他们是可疑人物似的。杨玄脸色冷了冷,但是脚步只迟疑了一下,还是非常光棍地一屁股坐了上去——这世界上能让她吓得抱头鼠窜的生物只有一种,就是大狗,鬼不行,人更不行。她旁边的黑衣男伸出手:“对不起杨小姐,能暂时保管您的手机么?”杨玄看了他一眼,反问:“我要是说不行,是不是显得很不识相?”这个黑哥们儿一声不吭,只是执着地像她伸出一只手,纹丝不动,活像一块望夫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