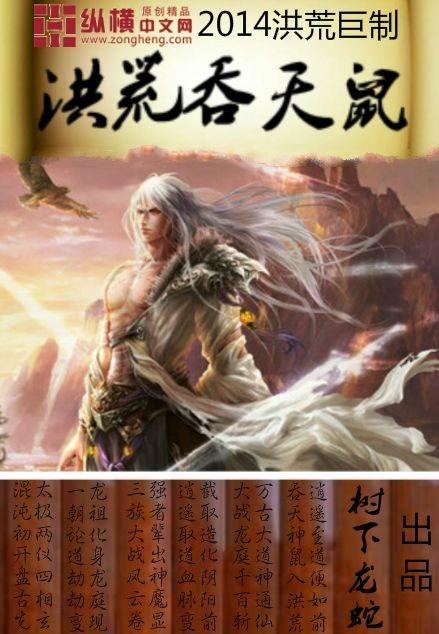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抢你没商量一女多夫 > 第九十三章 福无双至二(第1页)
第九十三章 福无双至二(第1页)
光给紫因的脸笼上层柔和的光晕,连疤痕似乎也不再他认真地注视着笑歌,疯狂似乎从来不曾在那双莹黑的眸子中出现,那种坚定的神气甚至令她有一瞬的失神。
真的可能吗?除了离弦和柯戈博之外,还会有男人不介意她的长相和身份?
紫因静静地等待着她的回答。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她仍只是呆坐着,拿种狐的目光打量他。
阳光撒在身上,融融的暖,他的心却一点一点沉下去,往着那不见阳光的冰凉。可,越是如此,想要抓住她的那种念头就越是强烈,他就越不肯将视线从她脸上移开。
“嫁给我,好不好?”
原本清亮的嗓杂进丝沉郁,他固执地想要一个答案。当然,纵是她拒绝,他也没打算要放过她。但还是想亲耳听见她说一个“好”字。
仿佛只有那样,藏在他心的那个魔鬼才会消失,他所有的不甘和痛苦才能得到救赎——只要,她说“好”。
笑歌掉了泥团,无意识地低头猛揪身旁的草。
这样认真神情出现在那个孤傲清高的少年脸上,让她心慌意乱,无所适从。
她读不懂疯子的心思,可以抓住重点,避开一切有可能引爆炸弹的因素。而此时此刻,他失了狂乱暴戾,眼眸平静地如一汪深浅不明的清泓,她反而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笑歌皱眉用力草连根拔起。不敢看他地眼睛。
离弦和柯戈博私下达成什么协议。她不清楚。但一生一世一双人。不论最终陪在她身边地是谁。她都觉得已经足够。不需要锦上添花。她也不应该再有从前那种为创造出胜过血缘地家人而把无辜者拖下水地想法。
那么为什么会犹豫?她感动了?还是不忍心伤他地心?她应当从不在乎会不会有人因为她地一句话或一个举动而受伤地。不是么?
沉默蔓延着。是难耐地僵持。紫因缓缓起身。收线。故作轻松地低呼。“看。一条大鱼!”
笑歌地嘴唇动了动。忽然想起个重要问题。忍不住把那草连土块一起朝他扔过去。紫因愕然回首。见她一脸气愤地指着嘴巴这才想起哑穴还没解开。愣了一秒。不由得大笑起来。
过了好一会,他蓦地将鱼扔回水里,过来抱起她,眼角犹有笑意,“没事。其实我不需要答案。”
对的,何必要答案。反过来想想,她完全可以摇头拒绝,但是她犹豫了说明心里并不是没有他——这样,已经足够了。
额?啧!原来是在耍她!
笑歌恼了,张牙舞爪去挠他的脸。紫因居然猛地放开手,让她摔了个七荤八素。
虽然地上有草,但pp毕竟是肉做的。笑歌疼得直想哭,刚想伸手去揉。他却低喝一声,“别动!”????笑歌探头往下一看,只见一团花花绿绿的肉泥里呲出几根毛茸茸的长腿已辨不出是什么虫子。不过瞧那艳丽的色彩,毒性一定不小。她不禁打了个冷战意识地攥紧了他的衣襟。
“没事,蜘蛛而已。”紫因柔声抚慰乎真的不是什么大事一般。
可他不但眼神不对,连鱼竿和轮椅也扔下,只顾抱着她走得飞快,笑歌顿时疑心大起。当下便装作惊魂未定的模样抱紧他的脖子,偷偷越过他的肩膀往后瞧去——依旧是绿草如茵,水流轻缓,岸边除了那轮椅和鱼竿,并无可。
如果真的只是一只蜘蛛而已,他又为何这般匆忙急于带她离去?笑歌不解地蹙起眉头,忽觉背上痒痒热热,忍不住伸手去挠。
这本是个寻常的动作,紫因却立时变了脸色,低声命令道,“别挠!忍忍,回去再说!”
笑歌只得缩回手来。那痒热的感觉却不止没有消失的态势,反而越来越强烈。就如同有什么东西沿着脊背向上一路攀爬,停在那肩胛骨间盘桓不去。
待到了胡家,紫因抱她径直进了东厢里间。关紧全部门窗,方回头坐来床边,毫不客气地把她按倒,拿剪刀唰唰几下将她的衣服后片剪开来。
肌肤接触到冷空气,笑歌才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事。一时间羞恼交加,想撑起身子来跟他拼命,紫因却忽然解开了她的哑穴。
“哪里难受?快说!”
声音又低又急,显然并不是为着她想到的那些龌龊缘由。笑歌一愣,不明白他究竟在慌什么。空气里的冷令那种痒热感愈发清晰,简直叫人忍无可忍。苦于无法起身,她只得反手去够,“背上好痒!”
紫因忙抓住她的手,又细细检视一回,皱眉道,“只有背上痒吗?可你背上除了宗主之印,没别的东西。”
宗主之印?
笑歌茫然。却是无暇思考,也顾不得什么形象不形象,趁他松开手,忙大力抓挠。可惜没练过瑜伽,
够不到肩胛骨那块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