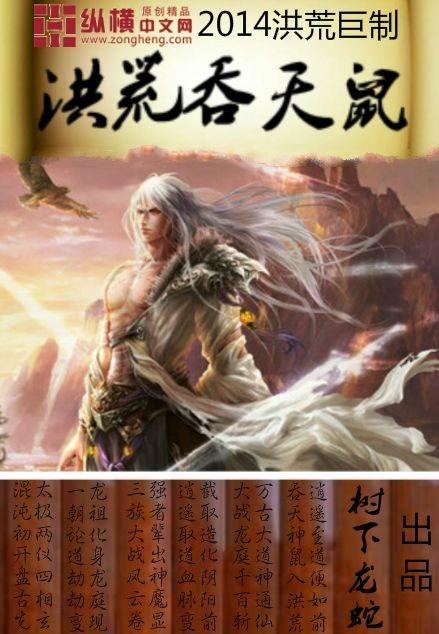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易次元诸神令 > 第十八章 第一次尝试失败(第1页)
第十八章 第一次尝试失败(第1页)
也许原来的柳如斯早已不复存在。老师同学们第一眼见了他,都大吃一惊。
脸色苍白,头发蓬松,形如枯槁。
同时,开学后,他的每次测试成绩也呈直线下降。
随着柳如斯成绩的下滑,曾琪时开始心急如焚了。
她想起了柳如斯曾经告诉过自己对于这个世界仿佛曾经经历过一般之类的话语,当时她还有些嘲讽他。
可是,现在回头想一想,“也许柳如斯说的对”,曾琪时尝试着说服自己。
三月的天气,就像初经恋爱的小姑娘的脸色,一会红扑扑的,一会又假装气恼的样子。
夜晚,曾琪时辗转难眠,她想了一晚上也没有想通这个问题。
于是,她思索着是否将这个问题告诉给了史从兆。
一次,借与史从兆讨论问题的功夫,她试探性地询问道:“哎,你最近有没有发现柳如斯有点变了样?”
“你是说变了个人。”
“对。”
“嗯,我也这样觉得的。”
“你仔细说下。”
“我觉得柳如斯好像受了什么打击,变得性格孤僻,不通情理了。”
“嗯。”
“我觉得我们应该帮他一把,毕竟作为兄弟,就应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是啊,现在柳如斯有困难了,我们不能袖手旁观。想想我成绩差的时候,是他辅助我的课业;我生病的时候,是他忙前忙后。”曾琪时早已焦头烂额了。
“你再想想,他曾经给你说了些什么没有?”史从兆也有点心急了。
“有。”
“那你快说。”
“就是柳如斯曾经给我说过,他觉得这个世界似乎对他来说有点似曾相识。”
“似曾相识?”史从兆反问道。
“我也讲不清楚,他对这个世界,他感觉自己好像活在梦里。”曾琪时说话有些结结巴巴了。
“会不会是他有心理问题了呢?你觉得呢?”
“我觉得有这个可能。”
“不如我们将这一切告诉他,或者告诉他的父母吧!”史从兆提倡到。
看曾琪时有点犹豫,史从兆继续说,“这可不是小事,你看每天电视上精神病的事例还不够多吗?我们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好,我早就觉得有这个必要了。”曾琪时转头想了想,说。
就这样,柳如斯趁着课件的10几分钟时间,时常为同学们讲授课外知识,什么四维空间、黎曼几何,费马猜想等等,他都有涉及。
甚至于老师的上课都无法正常进行,在无计可施的办法下,老师只能通知同学们开家长会。
“有个别同学,甚至私下里组织社团,妄图阻止老师的授课”,班主任在家长会上呛声到。
“柳如斯的家长,家长会开完后,请您留下来”,这显然是对柳见戈说的。
“唰”的一声,家长的头齐刷刷的超柳见戈望去,这让他很是没面子。
回到家里,父亲柳见戈对着儿子就是一顿血口喷头的臭骂,但是柳如斯不但陋习不改,反倒是更加振振有词了。
就这样,在父子间不断发生冷战,无法和解。
晚上,他母亲说道:“也不知道这孩子怎么想的。”
“不如让曾琪时劝劝他,或许有效。”
果然,柳见戈将这件事告诉了曾琪时的母亲姚从逝,姚从逝也转告给了曾琪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