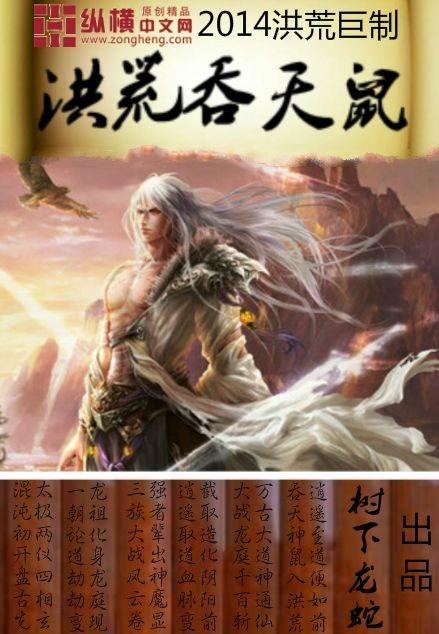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女装大佬在明朝笔趣阁 > 第27章(第1页)
第27章(第1页)
“怎么了这是?”李乘风不解,是有人欺负她俩了吗?按妙清的性子来讲,不太应该吧。
见他清醒后二女微愣,随即双双扑过来,激动道:“靖华师父!您终于醒了!”
“感觉怎么样?想喝水吗……”
“身上哪里不舒服?要不要奴婢去叫人……”
李乘风有些受宠若惊:“我无事,只不过睡了一觉,并无大碍。”
“睡一觉?”妙清夸张的大叫:“师父,您整整睡了两天了!”
李乘风不敢相信:“我睡了两天?”
“是的,您不知道,这两天世子都来好几次了,每次都要请大夫。但是我们谨记您之前吩咐过的,您说自己教派内有规定,不能接受他家教义和治疗,否则会被逐出师门,十几年修行功亏一篑。我们一直拦着,世子都下最后通牒,再不醒明天大夫就要过来了。”
李乘风听罢不由后怕,还好自己留了一手!倘若来个大夫一把脉,自己可就全露馅了!连忙感谢自己两个小跟班。
不过要说李乘风这一觉,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最起码他目前最大的心病——兴王百日祭,就这样糊里糊涂的被自己睡过去了。不用主持祭奠着实是让他松了口气,如今只要伪装好身份,别掉马,基本上就万无一失了。
想到这里,李乘风心情大好,挣扎着起身下床,趁着外面天亮,想去透透气。
谢绝了两个小丫头的搀扶,努力伸展了两下,就听见身上关节啪啪作响的声音。李乘风不由苦笑,感觉他好像是个七八十岁的老大爷。此时天气正好,温煦的阳光晒得人微微发汗,李乘风眯起眼,享受这难得的宁静。
“贱蹄子命真硬,那帮歹人怎么没弄死你!借着世子的光被救,这才几天又出来撩骚!”得,白感慨了,心中翻起大大的白眼,不用猜他都知道是谁。
只见郑寡妇扭着腰走进小院,满脸的尖酸刻薄。她之前诬赖李乘风结果被沈涛及时打脸,再加上蒋氏整治府内下人让她损失了不少,不过她为人虽然讨厌,但确实小心谨慎,没抓到什么直接把柄。蒋氏忧心儿子安危,也没怎么深究,就只罚了几个月月俸。
虽然没有伤筋动骨,可王府里都是些什么人啊,正应了那句话,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大家都是看人下菜碟,见郑寡妇失势,身边心腹们树倒猢狲散不说,就连其他管事也都趁机挤兑,把最苦最累的活交给她。
李乘风他们回来的那两天郑寡妇刚好被派去乡下检验田庄,所以也太清楚怎么回事。刚回来便听说那女道士完好无损的躺在清江观里,一股邪火直冲天灵,飞速跑过去想那对方撒气。
李乘风本想刺她两句,结果见她灰头土脸,仿佛老了好几岁的样子,心中一乐,决定大人有大量不跟这老娘们儿一般见识,转身就要回屋。
郑寡妇哪里容他走,反手便拦住去路,音量越来越大:“怎么?有能耐做还不让说?我今天就让人听听你的那些男盗女娼的破事儿!成天在这装得像个人似的,以为抱住了世子的大腿就能……”
“就能怎么样?”
李乘风刚要回嘴,就听见一道暗含怒气的声音响起。回头一看,已经恢复锦衣装扮的朱厚熜冷冷站在门口。
起先郑寡妇还没反应过来,过了好一会儿才回头,见朱厚熜连忙行礼。眼睛转了两下,计上心来,哭诉道:“世子爷!您可要给奴才做主,这女道士之前就跟刘力不清不楚,现在回来后在这清江观里简直目中无人,奴才怀疑您被绑,说不定就是她跟那些人里应外合,所以才来质问。”她心知朱厚熜疑心重外加性格颇为自负,只要提一嘴,就会顺着想下去。
世子还是那副淡漠的模样,看不出喜怒:“哦?这么说来孤还要感谢你。”
“为世子分忧,是奴的荣幸。”郑寡妇陪着笑脸点头哈腰。
“混账东西!”朱厚熜暴喝:“欺上瞒下,颠倒黑白,王府怎么养了你们这一帮狗奴才!”他刚刚被下人陷害,此时正瞧谁都不顺眼,在他眼里,郑寡妇跟刘力简直就是一丘之貉。
想到来时所见,李乘风被人指着鼻子骂,心中又是一阵烦躁:“来人!把这狗奴才给孤拖下去!”接着不理会瘫软成一滩烂泥的郑寡妇,转身看向李乘风。
对于郑寡妇的下场,看朱厚熜的表情,李乘风心中也有数了。他不是圣母,现在只觉得一阵痛快,连对面小屁孩儿趾高气扬又故作深沉的表情,此时看着也觉得可爱起来。
朱厚熜站着伸脖子等了半天,也没等到对方的答谢,不由怒道:“你平时不是挺厉害的吗?之前跟孤那副牙尖嘴利的劲儿呢?还自诩身手了得,怎么让个奴才在你眼前耀武扬威的。”
李乘风无语,那老娘们儿是气人,但他也不至于动手打女人吧,小世子当时不比这讨厌多了,他不也没怎么用武力吗。也不接话,只开口问道:“世子爷来找贫道可有事?”
感谢没收到,对面态度还冷冰冰的,朱厚熜心中郁闷,带着几分委屈道:“孤一直让人在这守着,听说你醒了马上放下手中事就赶过来了。”
李乘风恍惚中仿佛看见一只垂头丧气的小狗耷拉这耳朵。摇摇头,迫使自己清醒一点,心中默念几遍这是未来的嘉靖,未来的嘉靖!调整好心态后才回道:“感念世子挂心,贫道自幼在山中修行,此次全当磨炼心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