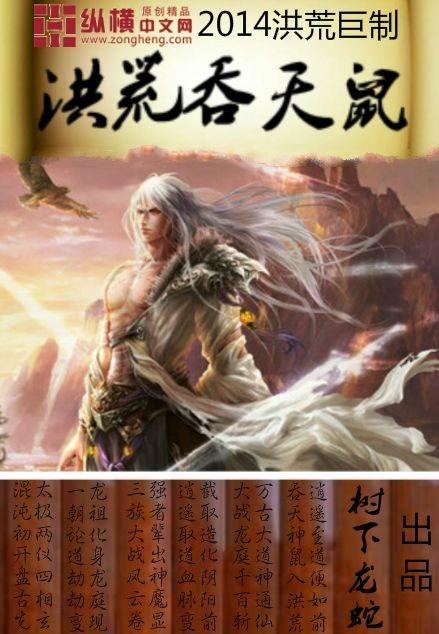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我在虐文权倾天下快穿帝国王储 > 第26章 霸道王女和她的小娇夫26(第1页)
第26章 霸道王女和她的小娇夫26(第1页)
启光二年,春闱放榜。
会试金榜历来设张贴在贡院,可候在贡院近处的多为小厮或书童,下场的考生鲜有亲去看榜的,反多会矜持的选个远离贡院的地儿等着人来传名报喜。
而这当中最热闹的还要数城南状元楼。
为讨个彩头,状元楼上缀着红绸红花红灯笼,正楼外两侧匾上龙飞凤舞的题着十四个大字──
此去蟾宫应不远,诸公继踵上天梯。[注1]
此时楼里人声鼎沸,这般的热闹中却夹杂着一丝不同寻常,原因无他,这满是秀才公的大堂里正坐着几个姑娘,显得十分突兀。
“何不去雅间里等?”发问的是一身着云山蓝光锦的姑娘,乌鬓未点珠簪花,只素净的用一云纹木簪挽着,她说话间脸颊微红,想是有些许窘迫。
钟怡嘉的窘迫更贴切的来说,应该是怯懦,对与众不同的怯懦。
这里的读书人虽各有各的小圈子,可此时的氛围极热烈,素味平生的人相互间谈天说地,难免再交几个志趣相投的新友,唯独她们被严丝合缝的挡在屏障之外。
自是不屑于对视的,那些男子端着一副矜持清贵的模样刻意对她们视而不见,而阴暗处无形的鄙夷却又无时无刻不在戳着钟怡嘉的脊梁骨。
甚至都算不上文人相轻,钟怡嘉可以很清楚的察觉到,那些人的言行举止间仅仅只是在表达对女子存在的排斥。
而坐在钟怡嘉对面的王嫣然闻言只是呷了一口茶,从容道:“同是等榜,为何要避?”
摄政王殿下能给的只是机会,而将来为臣为官为天下先的骨气却要靠她们自己去争,如果此时羞于己而避让他人,那将来立于朝堂之上,是争还是不争?
今日是状元楼,明日便是天子堂。
王嫣然心悬明镜自然再清楚不过,今日她们但凡退一步,来日女官处境便要退万万步,朝堂如沙场,退则万劫不复。
这就是她一定要选在状元楼的原因,要让天下人的眼睛都看着,看着她们寸步不让!
既能被摄政王亲点参加女科取士,钟怡嘉自然不会是什么庸碌之辈,她几乎瞬间领会了王嫣然话中的锋芒。
同为等榜学子,她们凭什么要避?
钟怡嘉鼻翼微动,轻轻吐出一口浊气,只觉得心中豁然开朗。
随即,她整理好自己心中的紧张不安,学着王嫣然的从容坦然去无视周遭的恶意窥视。
只可惜视而不见对小人来说无甚大用,特别是嘴碎的小人。
方才王嫣然讲话并未压低音量,她的话自然也就不只是钟怡嘉一人听到。
“只怕等来的是大梦一场空。”伴随着一声轻蔑的嗤笑,旁边桌响起了极其刺耳的讥讽声。
循声望去,开口说话的人穿着一身斑鸠灰灯笼锦,鼻头肥大好似猪胆,双眼细长而下垂,两撇稀疏的胡子努力黏在嘴皮上方,势单力薄的为这样一张脸撑起零星半点的斯文。
灯笼锦为金织锦缎,穿的人自然是非富即贵,可说话这人看上去面生得很,并不是王嫣然认识的燕京世家子,想来是个外地考生。
林文耀确实不是燕京人,故对燕京这些世家贵女不太熟悉,再加上方才替他看榜的小厮来报喜,三百一十六的贡士出身多少令他有些飘飘然。
他对自己的斤两很是清楚,若不是摄政王执意加录二十,他如今已怕是名落孙山,说起来还真要感谢感谢那荒唐可笑的女科。
可林文耀倨傲,最看不起的便是女人。
自然而然,夹讥带讽的恶语脱口而出,而随着话音落下,原本热闹的状元堂忽地一静,陷入一种诡异的凝滞中。
怎么可能真的不在意那几个女子,只是众人要么碍于读书人的清高,要么畏惧世家贵女的身份,都不太愿意作出头鸟,起口舌是非。
而此时此刻,既已有人先开了这口,状元楼先是一静,随后更热闹了几分。
林文耀起先见周遭安静,心中还咯噔一下,后又见其余人纷纷投来赞赏、附和,一种被追捧的感觉当时就令他上了头,仿佛盛夏饮冰,浑身舒爽。
大受鼓舞的林文耀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故意用评头论足的眼神上下打量了对方几下,他想着姑娘家脸皮薄,等着对方气急败坏的跳起脚,他正好引经据典将人羞回家去。
不料对方只是以一种看杂耍猴戏的表情,轻描淡写的看了一眼便移开,紧接着红唇微勾,虽是无声,却又说不出的嘲弄。
到底是个小肚鸡肠的,林文耀被这么一看,只觉得轰的一声血液从脚底冲向了脸颊,当下说话就更不讲究了:“三甲唱名怕是快结束了,那井底之蛙总不至于是在等五魁吧,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