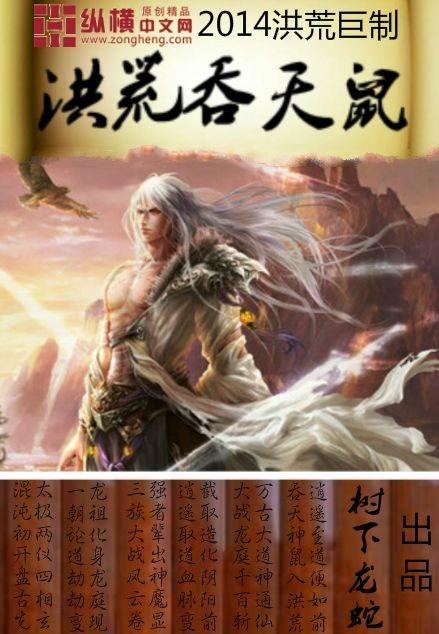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是辞离亭宴 > 第17章(第1页)
第17章(第1页)
一席话说得柳少保不禁有些汗颜,萧清规辅政四年,他身受儒学之道熏染,怎可能对她没有微词,更与吕文征想到一处去,多少认为萧清规是在担心自己的身后之名,只不过他比吕文征圆滑了些,萧清规待他谦逊,凡事以理相商,他便也会将表面功夫做好。
只不过他没有想到,看着萧清规眉目间淡淡的愁色,让他忍不住对自己过往的看法产生一丝怀疑,因为他下意识觉得,她似乎是倦怠于公主这个虚名的,更别说越权揽政满足自己的野心了。
柳少保低声称“是”,萧清规便挥了挥手,命他兀自去忙,不必理会自己。
她每每来翰林别院绝不久待,看得出那些学士很是拘谨,身长八尺的男儿个个在她面前露着个后脑勺,她也觉得压抑。
寿眉适时上前扶住萧清规的手臂,提醒道:“长公主,该回宫喝药了,今日可还午憩?”
萧清规早就瞥见了她匆匆入内的举动,问道:“何事?”
寿眉连忙说:“王爷叫人来传话,说长公主的寿礼到了,请长公主到千秋寺一见。”
萧清规正要迈步上辇,闻言停住了脚步,顿了片刻才答寿眉:“什么礼还得我亲自去拿?排场倒是不小,他既如此视如珍宝,倒也不必割爱。”
寿眉是听到了风声的,知道那尊大观音像无法入宫,只能暗急自己嘴笨,又缺乏一颗玲珑心,不知当说不当说。若是不说,萧清规怕是定不肯去的,若是说了,岂不是坏了萧翊专程准备的惊喜?
一路上寿眉都忧心忡忡的,萧清规看得真切,觉得有些好笑,她倚重寿眉、相信寿眉,正是看重她心实。可也因心太实了,多了些愚钝,她或许应当指点寿眉几句,无需事事皆依从萧翊,到底是她嘉宁宫中的人,又素来尽心,萧翊岂会因一件小事便怪罪。
步辇平稳的行在御道上,萧清规闲适地歪着身子,抚摸怀中的手炉,刚临近宫廷西隅,还未进嘉宁宫,她先是看到一方巨大的阴翳,视线从寿眉身上移到空中,顿时也是一愣。
三丈红墙之上,唯见水月观音半身像,青石如玉,金光加身,直耸入云,屹立于千秋寺内院后方,庇佑着脚下林立的静室香堂、九重三殿。
她在宫内向高处看,不过是远瞻,瞧得并不够真切,也正因不够真切,反而更能看出那菩提宝相的玄机,不觉有些惶然,久久说不出话来。
“关州崇山多歧路,断送崖下万佛香。”陆真颜刚入宫,迎面停在步辇前,出声唤回了萧清规的神智,“西骊改关州为兰弗城后,万佛寺惨遭破坏,只剩这一尊最为殊胜的水月观音,近百年来中原已无人见过其真容,王爷这份礼委实太过劳民伤财了些。”
萧清规转头看向他,语气有些冷淡:“你怎么进宫了?”
“真颜再不进宫,殿下怕是要将真颜忘却了。”
陆真颜语气中挂着明晃晃的委屈,半个多月前,离亭赐宴的风波结束,萧清规便命他回了千秋寺,始终没有召见,态度甚是冷漠。他起先还不知自己做错了什么,前去离亭穿青衣、散青丝,故意惹恼太后,乃是萧清规授意,她定然不会因此与他置气。
直到他灵光乍现,想起八月十四回宫那日,萧翊在嘉宁宫与萧清规下棋,他不过是出言讥讽了萧翊一句,自认说得并不过分,可萧清规还是不悦了。
他不如萧翊那般了解萧清规,萧翊是最知她擅长用钝刀子杀人的,陆真颜自从跟了萧清规便没受过这等凌迟的折磨,显然是沉不住气了,直接擅自入宫。
寝殿内,地龙已烧了将近足月,暖意深沉,萧清规坐在榻上,左手挂着那条十八子念珠,右手捻着双象牙白玉香箸,拨弄错金炉中的香灰,颇为闲适。寿眉坐在对面,小心沾了个榻沿,正在为萧清规煮茶,用的是昔年南荣进贡的茶具,小火慢煎,费尽功夫。
唯有陆真颜站在一旁,碍于寿眉还在,有些话不好出口。
总算熬到寿眉煮完了茶,双手捧到萧清规面前,萧清规品过后才问陆真颜:“观音像入寺,你不在寺中安排,入宫为何?”
“王爷办事素来周全,何须我这个寺主为其安排。今日是六斋日,香火极盛,可拜王爷所赐,已提前闭寺,真颜无事可做,愈加想见殿下,故而违令入宫,殿下责罚便是了。”
这话又是暗中带刺了,明面上说萧翊办事周全,实则是在为萧翊擅自做主入千秋寺而不满。萧清规半掩在袖中的手搓动着念珠,闻言嘴角泛起一丝不算笑容的冷笑,又跟寿眉说:“这方山露芽倒是甘美,也给真颜君品一品。上次内廷送来的檀香有些燥气,你再去换些回来供佛。”
寿眉给陆真颜斟了杯茶就出去了,房中只剩下他二人,陆真颜哪有品方山露芽的心思,一见寿眉将门带上,就上前半跪伏在萧清规膝头,讨好地叫着“殿下”。
他是最爱叫她“殿下”之人,不像寿眉或其他宫人皆恭敬地称“长公主”,陆真颜每每这般唤她,总是带着些氤氲暧昧和绵绵情意的。
萧清规伸指挑起他的下颌,直观他那副我见犹怜的模样,红颜祸水一词岂可单指女子,放在陆真颜身上也未尝不可,任是萧清规铁石心肠也不免心软。
“反省了半月有余,可知错了?”
“真颜知错,只是不肯认错。可殿下若是为此动怒,那真颜即刻便认,只要殿下开心。”
“既然如此,便还是不知。”否则何来的知错又不认错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