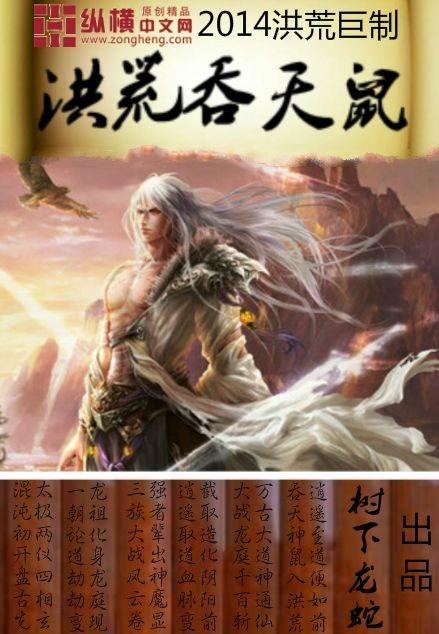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首长一抱双喜全文免费阅读 > 第184章 绿茶(第1页)
第184章 绿茶(第1页)
办公室内,老人面前摆着升腾着袅袅茶烟的敞口杯。
暮寒珏信步进来,慢条斯理地在季宏策对面坐了下来,悠闲地翘起了二郎腿,把季宏策气了个半死。
“你到底是怎么搞的?婚姻大事怎么都不知道和长辈商量一下就擅自做主!”
季宏策狠狠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杯中茶汤随着震荡的波纹从敞口上泄出,湿了茶几。
暮寒珏不带任何情绪地瞥着他,稳坐如钟。
“暮远剡和林柚入土二十年了,我那短命鬼姑姑也死得不明不白连尸首都找不到,您算我哪门子的长辈?”
这一句话噎得季宏策上不去下不来,暮寒珏还偏偏悠闲地从茶盘里给自己也挑了个杯子,端起茶壶朝杯中续上茶汤。
热水激荡着茶香,暮寒珏挑眉,“墨砚倒是会孝敬您,把我这最好的茶都拿出来泡上了。”
他端起茶杯,轻轻顺着杯沿吹了口气,送入口中。
“绿茶降火气,您老要是不喝也别浪费。”暮寒珏掀起眼帘,示意桌上的那一圈水渍,“要是为了这点水花就让我这桌子报废了,值得么?”
久居高位,季宏策听得出这话里的另一层意思。
暮寒珏是在提醒他,如果他胆敢因为外界那些讫无定论的风言风语就对余依有所动作,就不要怪他翻脸不认人掀了他的总统府。
他和暮寒珏之间,除了炎国的利益之外,早已没有其他可说。
这些年来,季宏策面对暮寒珏时常觉心中有愧,却又拉不下脸来去向一位晚辈道歉。
没了暮寒珏父辈那些人的维系,那点摇摇欲坠的亲情显得尤为可笑。
季宏策在这里以长辈的名义去训诫暮寒珏,确实有失体统。
“婚姻大事不是儿戏。”季宏策摆正了身子,皱眉说:“你现在位高权重,年轻力壮,是往上再走一走的好时机。娶一个对你没有任何帮助的女人,还要连带着你的名声也一起抹黑,这样的婚姻要它有什么用?”
“哦?那阁下的意思是,我连决定自己跟谁在一张床上睡觉的资格也没有?”暮寒珏眯起眼睛,嗤笑道,“这算哪门子的位高权重?”
季宏策强压着心里翻涌上来的火气,耐心解释:“我有意撮合你和悠言,那是一桩好婚,你要是能应下,也算是我能给你的亡父亡母一个交代。”
暮寒珏瞧了他一眼,挑唇笑了。
“既然三句话离不开我那早死的爹妈,不如阁下还是打道回府,请几位大师来跳跳神。”暮寒珏声线渐冷,“兴许您能有机会当面给他们交代。”
“寒珏!”季宏策疾言厉色起来,“你也是个要奔三的人了,不要不识好歹!你还以为自己是八年前的毛头小子,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吗?”
暮寒珏向后仰了仰,长臂慵懒地搭在身后的靠背上,五指向下自然垂着,看向季宏策时,那双狭长的丹凤眼中盈满戏谑的意味。
“原来阁下还记得八年前都发生过什么。”暮寒珏语速缓而沉,“那么,阁下还记不记得我这条险些废了的胳膊是拜谁所赐呢?”
“你……咳咳咳……”
旧日之事被蓦然刺穿,像是扯下了一块时过经年的遮羞布。
一条横跨在姑侄之间的沟堑任凭何人再去努力也无法填平。
季宏策看着暮寒珏那一副漠然的表情,其实心里也很想解释。
使用那些药物,不是他的本意啊……
思绪恍惚回到八年前,彼时还是少年模样的暮寒珏在暴戾滂沱中任雨水浸湿头发,从身上滚落。
少年像鹰隼般阴鸷的双眸紧盯着他,手中的枪上了膛,随时可能从枪管中爆破出裹挟着火舌的弹片。
那时候,季宏策好心提醒过他的。
“寒珏,把手里那东西放下,今天的事我便可以当做从没发生过。”
“我做不到像阁下您一般缺寡情薄义。”少年挑起冰冷的笑意,声音如切冰碎玉,“让你的人放我走,否则掀了你这总统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