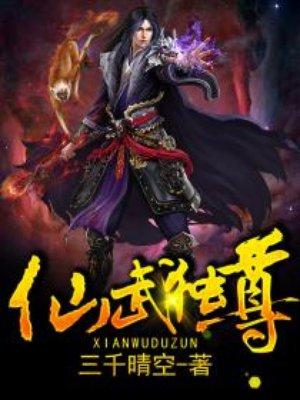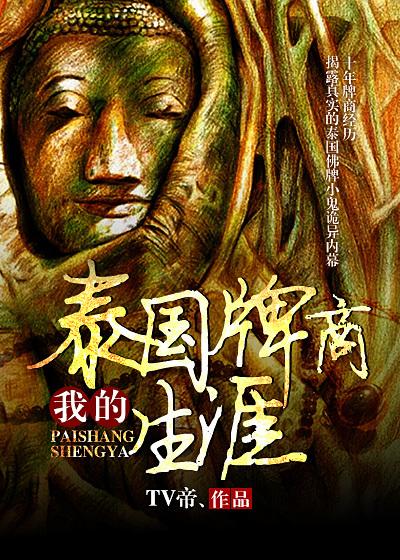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组织部长百度百科 > 第37页(第1页)
第37页(第1页)
“徐文俊这次在我的问题上,的确是帮了我的大忙。知恩不报非君子。我本来想借徐沈平的房子要装修的名义,再给他送点钱,但是又考虑到这样直来直往地送钱,做法不够艺术。思前想后还没想出个更好的办法。如果把徐沈平的事情处理得体,让徐文俊和沈彩虹满意,下一步再进行你的调动工作,就会事半功倍。”王悍东听了章建国的想法,似乎不无道理,章建国并没有把他的事情放置脑后,而是讲究策略和艺术,看来他对章建国的种种不满是冤枉了好人。他想起自己以前天天在背后骂他,有点小小的后悔:“现在你再去给徐文俊送钱,可能不是个合适的时机。不过当时徐文俊把徐沈平弄到市交通局来,不就是要你为徐沈平谋一个好出路、好前途吗?你现在在市交通局里大权独揽,‘党、政、军’一把抓,是帮助徐沈平很好的时机。另外,常言道‘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你要在交通局里大展拳脚,就必须有一支自己的御林军,有一帮自己的铁哥们。你如果把徐沈平提拔到关键的位置上来,比如白送他一个局党组成员之类的官,徐沈平能不和你巴心贴肺吗?你是花钱买的官,局党组成员也值不少钱!送官就是送钱。这样你既帮了徐文俊、徐沈平,也是帮了你自己,岂不是一举两得?假如我有可能再调到市交通局来,市交通局几乎就是我们的天下了。”王悍东的点子经常是出其不意。章建国奇怪自己怎么没有想到这个看似简单的主意?但是他对王悍东后面那个提议心存戒备。王悍东老奸巨猾、老谋深算,他对王悍东要多加小心,防止引狼入室:“你前面说的那个主意不错。徐文俊曾经要我多多关照徐沈平,现在我有了关照徐沈平的客观条件,如果没有关照好他,徐文俊心里一定不满意。让徐沈平做局党组成员是否妥当,我回去再慎重斟酌一下。后面你说的你也想调进市交通局来,你真有这样的打算?你现在的级别是副局级,你调进来还是副局长。这个问题你可要想好了再说。交通局的局长和煤矿里的矿工一样,都属于高危险性的职业。河南省的三任交通厅厅长都成了阶下囚,国内还有几个省的交通厅厅长也都被栽了。现在全社会有多少双眼睛都在盯着交通厅、交通局。交通局的保险系数比你们银行低多了。”王悍东听了章建国的话,猜测他对自己存有戒备,得想办法打消他的顾虑:“章局长你的话不无道理。我听说有过这样的戏言:‘如果你喜欢一个人,送他进交通局;如果你痛恨一个人,也送他进交通局。’管公路建设能让人以最快速度‘富起来’,也能以最快速度‘倒下去’。交通局和煤矿在安全问题上有某种共同之处。但是煤矿事故频繁,是因为煤矿领导不重视安全工作,所以才会频繁地发生透水、冒顶、瓦斯爆炸等等矿难。交通局局长出事,也是由于他们自己的运气不好,没有做好自己的安全防范工作。你同样也是交通局的局长,你为什么没出事?如果你真是要出点什么事的话,事情早就出了。你讲的只是远虑,起码我们没有近忧。我们能够安然无恙,主要原因不外乎两条,一个是我们做事的手法,比那帮落马的蠢材高明,另一条就是我们在上面有人罩着。如果把我们以前做过的事情给抖搂出来,不管用哪个国家的法律来量刑,我们都是罪犯。罪犯只有现在,没有未来。俗话说‘今日有酒今朝醉,明天倒灶喝凉水’。你现在想得那么多,不是自寻烦恼吗?”章建国让王悍东的话给吓了一跳:“不想怎么行?现在不想到时候再想就晚了!”“我看我们的事情没有那么严重。你刚才说的只是从最坏处打算,但是我们要向最好处努力。你回去抓紧把徐沈平的事情先落实下来,有了徐沈平就有了徐文俊,有了徐文俊就有了我们。我的事可以再往后放一放,等我们先把徐沈平的事情摆平了,我的事情再从长计议吧。”章建国给王悍东的话搞得没有了情绪,不想再谈下去了。章建国上了十楼,周丽下到九楼。两对野鸳鸯各自安歇,一夜无话。一个星期天的下午,琼花在沈彩虹的监视下,在沈彩虹的卧室里擦洗地板。突然卧室电话的铃声响了起来。沈彩虹拿起卧室里的电话,简单地应答了两句话,她下意识地朝琼花瞟了一眼,可能是电话的内容有关机密,不能让琼花听到,沈彩虹就把卧室里的电话听筒搁下,到楼下客厅的电话分机上去接听。琼花并没有注意到沈彩虹的离开,继续擦她的地板。琼花擦地板擦到床前的时候,床底下一个纸箱的一角突出了床沿好几寸,妨碍了琼花擦洗。为了把地板擦得更干净,琼花把纸箱向里推了推。她原来以为纸箱不会有多大的分量,就轻轻地往里推了一下,可是纸箱挺沉的,躺在那里纹丝不动。琼花出于好奇,想看看纸箱里究竟装的是啥。她回头看了一下,沈彩虹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走开了,她就大着胆子把纸箱拖了出来。她打开没有封口的纸箱,看见里面是好几个四四方方的纸口袋,每个口袋上还写有不同的阿拉伯数字和人名。琼花打开一个纸口袋以后,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里面竟是一沓沓的百元大钞。整个箱子里究竟装了多少钱,她一时无法估计出来。这时她听到木楼梯有了动静,是有人上楼来了,于是她匆匆忙忙地把纸箱推回到床底下,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擦她的地板。琼花因为惧怕沈彩虹看出什么端倪,紧张得心在胸腔里怦怦乱跳。沈彩虹进了卧室,她把搁在一旁的电话机听筒挂好,又环顾了一下四周,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继续站在旁边监督琼花擦地板。琼花因为偷看了她不该看见的东西,心里有了一丝内疚,甚至是负罪感。她草草地把地板擦干净,没敢正视沈彩虹一眼,就匆匆地下楼到厨房去了。琼花在厨房里一边准备晚餐的饭菜,脑子也一直在转个不停。她刚才在楼上看见的钱,是她今生今世看见的最大的一笔巨款,就是老家三十里铺的农村信用社,也未必有这么多的钱。东家不但官做得大,钱也出奇的多。她想不明白的是:城里当官的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钱?她甚至产生了一连串的梦想:咱如果有了这些钱的十分之一,哦,哪怕百分之一也行,那么咱爹就会过上好日子,咱也不用在外地做保姆,咱可以天天陪着爹,咱爹再也不会孤单寂寞了。但是这个美丽的梦想会变成现实吗?咱这辈子能有这么多的钱吗?……呸!做保姆的能够有口饭吃,就应当算是很不错的了,自己别在大白天里做白日梦了!晚饭以后琼花把餐桌和厨房收拾干净,回到自己的小天地里。她盘算着明天就是月底,她又该去服务中心领取这个月的工钱了。按照服务中心定下的规矩,她每个月可以休息一天。她上个月只请了半天假,两个月的休息日加起来,她这回可以连着休息一天半了。琼花以前在靠山村的时候,几乎是天天休息,自打做了保姆以后,她才体会到能够歇上一天半晌是何等的宝贵。在最近的一个月里,徐沈平因为忙于交通局的人事调整和东郊美庐新房的装修,平时很少在家露面,偶尔在家里遇上琼花也是行色匆匆。但是琼花总是感觉到在他的眼神里,有一种不可捉摸的东西在游动。琼花每次见到徐沈平,总会感觉到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安。徐文俊不是出差就是开会,即使是在家的日子里,他回到家里吃完饭,就一头钻进他的书房里,和琼花之间只属于点头之交。沈彩虹回家以后,经常颐指气使地指挥琼花做这做那。琼花在沈彩虹的淫威之下,没有半点的回旋余地,除了服从还是服从。琼花在徐家的两个月里,生活安定是安定了,可是心里除了孤独以外,只剩下了不舒心,总觉得有些压抑,靠山村自由自在的日子,仿佛离开她已经很遥远、很遥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