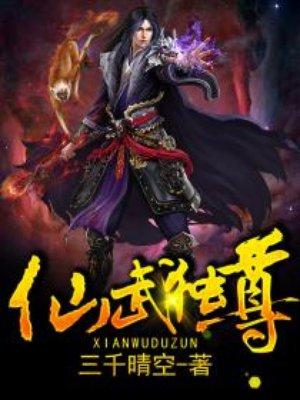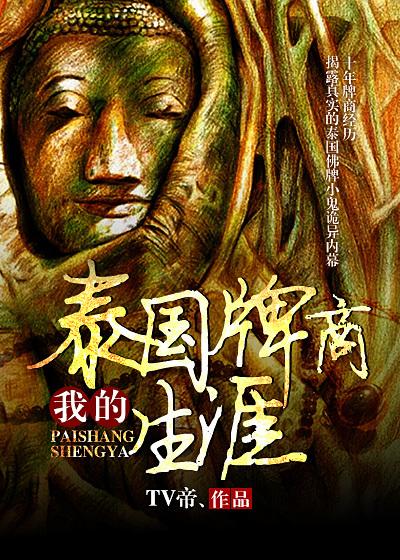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小时候打的疫苗胳膊上有花是什么疫苗 > 第70页(第1页)
第70页(第1页)
“很抱歉,我该回去了。”我起身付了侍者账单和小费,笑着对她摆手,“请允许我请你喝杯咖啡。”“孙郴——你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固执。我理解你,我可以等待,或者真的不行的话,你也可以在心中留一方给她,我不介意的。”“对不起,是你的话就真的不可以。我欠你太多,不能一直继续伤害你。”我微笑,“同样的祝福给你,学姐,我祝你永远幸福。”一如多年前,我在暧昧不清的月光下,在另一个女孩耳边声声的呢喃,我祝你永远幸福,你一定要幸福快乐。我的麦麦。我从未刻意去铭记任何事,只是关于她的一切,总是在不经意间就如潮水般奔流不息的涌出来。我回想往事的时候,偶尔也会迷茫,我为什么总是无法遗忘那个在槐树下对我微笑的女孩,那个整天跟在我屁股后面甜甜的叫我“小哥哥”的麦麦,我永远懵懂单纯的小姑娘。是的,她温柔婉约单纯善良,做事认真却没有多大的野心,是宜家宜室的好女孩,有成为贤妻良母的潜质,虽然她总是犯迷糊。但这是我总是放不下的原因吗?我不知道,可是我清楚,这并不能说服我自己。我想我虽然早熟,十五六岁的年纪还不至于计算的那么清楚。何况十几岁重逢的时候,她留给我的第一印象也只是个贪看帅哥的聒噪女生。跟身旁的同伴叽叽喳喳,一个劲的想看清我的脸,甚至不惜要换到对方的位子上。我只觉得厌烦,十五六岁的年纪,良好的家世,优秀的成绩,看惯了小女生痴傻的眼神,那个时候的我也是个被惯坏了男孩。我回头瞪她,她闪避不及,像个被当场逮到的小偷一样。我以为她会扭开头不看我,没想到现在女孩子素来不知道矜持为何物,狼狈之后,居然满脸若无其事地与我对视。我都忍不住要替她脸红。呵呵,我的麦麦,从小就脸皮厚,我怎么没想到。小时候她可以一整天跟在我身后,就算我厌烦了,赶她走,她也能死皮赖脸。我父母一直想要个女儿,麦麦就是他们最疼爱的小人儿。我妈说麦麦刚出生的时候,我比所有的大人都高兴,才两岁的小子非得要抱抱妹妹。我漫不经心的收拾着自己手头的论文资料,笑道,是吗?我小时候最烦她哭的。每次她一哭起来,气贯长虹,逼得所有人都得丢下手边的事去哄她。其实只要故意不理睬她,她还是会自己停止哭泣。逗她,问,你怎么不哭了。她会振振有词的哀怨,你们都没有人管我。那我哭给谁听?想起她晶莹如红苹果的面庞上委屈的泪珠儿,往事历历在目。我也惊讶,为什么那么久以前的事,我竟然还清晰的记得每一个细节,清楚的仿佛它们每时每刻都在我脑海中重新演练。我想大概是因为她已经不记得我们的从前,所以我要努力的去记忆,把她的那份也帮她一并记住。记住我们无忧无虑的童年。有的时候,人的感情完全用理智去分析,一切都是那么不可思议。命运的十字路口,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仿佛是不经意间的差别,就是天南地北的极端。我留下我的电话号码,在我知道她是我的麦麦之后。我叮嘱她一定要打电话给我,换回来的是一个寒假的坐立不安。开始时是在电话机前守了一个星期天下午,我想她回到家中一定会立刻打电话给我,于情于理,都应当报个平安。可是那一下午,偌大的家中,是呆滞的寂寞。我到底等了她多长时间的电话?一个寒假还是我整个十六岁的年华?我渐渐回忆不清,唯独清楚的是期待时的心情那时候大概就开始逐步微妙。再度重逢是在一中的校园。我看到梧桐树下的女孩,连跟高二的足球比赛都丢下。直到跑到她面前,我才惊讶的发现,我是如此的害怕她再一次从我眼前消失。这种潜意识里的恐惧,让我面对她时,只有满满的喜悦,而忘记了应该生她的气。是的,我应该生她的气,她不仅第一次没有认出我,第二次同样迷茫。傻乎乎的看着我,只差在脸上浓墨重彩的标注大大的问号“你是谁啊”。我失落的无以复加,甚至控制不了自己心头黯然的流露,你是不是已经不记得我了。“记得记得。”她重重的点头,燃起我微弱的希望,然后毫不留情的重重毁灭,“我记得你,你就是上次作文比赛坐在我前面的人。”说完了还一脸“好巧啊,真高兴在这里遇见你”的假笑。我的风度顿时维持不住,我无法解释我的怒火中烧。她根本不认识我!她的记忆中根本就没有一个这样的我!只有我才会把那些属于我们的过往牢记在心间。她承诺过会努力记得我,怎可这般言而无信。回首那一段青葱岁月,我也知道那时的自己是多么的莫名其妙。希翼一个三岁的小孩记住儿时的玩伴是不是太过强人所难。只是我钻进了牛角尖,无法释怀。为什么她会这么轻易的忘记我,在我还将她珍藏在记忆的深处时。是因为她身旁出现了新的人吗,她只会对他微笑,习惯性的依赖着他。我控制不了自己去关注她的一言一行。她的每一朵微笑,每一个蹙眉,我的情绪都会被轻易的牵动。可是她永远都不会知道,在她身后,有这样一双眼睛注视着快乐或不快乐的她。偶尔看到我,我目光锁定的这个女孩只会匆匆转头避开。柏子仁笑,孙郴,你这样是不行的,看上了就大胆去告白。我们学校,只要我不动手跟你争,怎么会有你搞不定的女生。我白了他一眼,粗声嘎气,淡漠的扯动嘴角,你想太多了。他要笑不笑地看我,轻轻逸出轻蔑,算了吧。算了吧,怎么可能算了吧。人的感情就是如此奇怪,明明知道迎不回她的任何回应,我还是忍不住去关心她。并不需要刻意,满满相似的黑色的人头中,我一眼就可以辨认出浅笑微嗔的她。我看着音乐教室里,站在座位的第一排上,她唱着《喀秋莎》。“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漂着柔曼的轻纱。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姑娘唱着美妙的歌曲,她在歌唱草原的雄鹰。……”旋律优美的苏联老歌,逼得人思绪不得不飞回很久很久以前。很久很久以前,那透过院子里老槐树的枝桠筛漏下来的阳光里,仰着头微笑的女孩,她在软软的叫唤“小哥哥”。我的唇角抑不住泛出笑容。“啧啧,呆鸟看傻妞,天生一对!”柏子仁一脸鄙薄的神色。我们要去楼上的教室练习跆拳道。“你老实说,这是第几次了,哪次不傻乎乎的盯着看上半天。”他一脸痛心疾首的神色,“孙郴啊,不是我说你,眼光能不能提高一点,初恋倘若毁在这样的女生手里,等你回想往事,会悔不当初的。”我沉默,对于这件事,我始终缄默。我怎么可能放弃对她的关注。她是我的麦麦啊,即使她已经不记得我这个小哥哥。她在冷风中着凉感冒,昏昏沉沉的趴在课桌上。我趁值周的机会溜到她面前,试她额头的温度。只觉得自己是多么的可笑辛酸,连关心也只能这样偷偷摸摸。她感受到了我的手,轻轻的吟哦出生,感冒的小脸带着病态的红晕。“我渴,我要喝酸奶。”她仿佛再自然不过的吩咐。我竟然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忙不迭的跑去买。想想,酸奶不好加热,而且不适合早上喝,我给她换了一瓶温热的鲜奶。没想到她喝了一口就毫不客气的吐出来。我以为我会生气,我向来不喜欢乖张任性的女孩,可是她略微皱着眉带着爱娇抱怨“我最讨厌喝鲜奶了”,只这一声,我尚未蹙起的眉头就舒展开来。听她如此对我撒娇,我的心情如万里无云的晴空。“如果不能喝酸奶的话,那么就换麦香型的纯牛奶吧。”记忆中的小小狡黠还没有遗失殆尽,闭着眼睛她也知道妥协,识时务者为俊杰。我跑到小卖部的时候,突然想起,她怎么知道早上喝酸奶不好,是谁告诫她的。一想到常常凝视着她的含笑的眼睛,我的心情就跌到谷底。是他吧,时时围绕在她周围,她习惯倚赖的他。也只有他,可以收获她的爱娇。我是怀着怎样的心情买好的牛奶,竟然还没忘记在微波炉里转上几圈。我机械的插上吸管,送到她嘴边。看她贪婪的喝着,带着满足的甜甜的笑容睡去,我又忽略了我应该生气这件事。我清楚的知道,这个笑容,她在睡梦中想给的是另一个男孩。可是这有什么关系呢?蹲在她面前,感受着她额头温度的,给她她想要的牛奶的,不是他,而是我!就假装,就假装,这个笑容她是全心全意的给我。我苦涩的微笑,一半清醒,一半沉沦;抑或是,清醒的看着自己沉沦。我想起我阅读的第一本英文原版小说《傲慢与偏见》,(无所谓特殊的喜好,只是我的英语老师推崇简?奥斯汀。)如果达西当初没有闲极无聊为了证明伊丽莎白配不上“美人”的称号而刻意去观察她,那么他大概不会爱上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