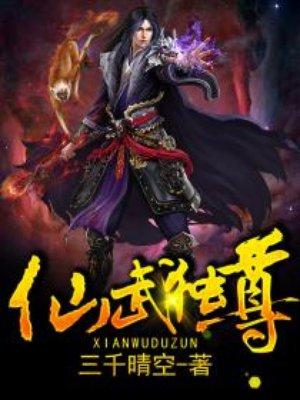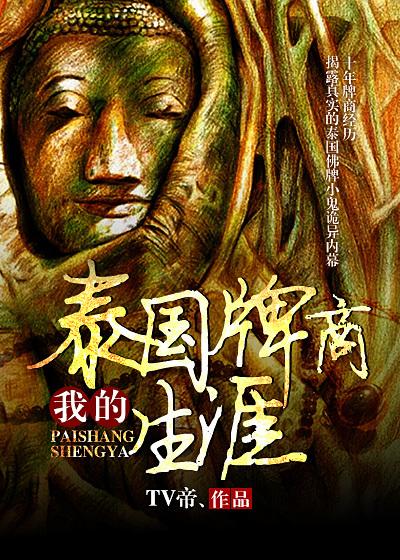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是什么意思? > 第76章(第1页)
第76章(第1页)
所以,在这段时间内。那位年轻的楚王又做了哪些事情?
“凤楚公主出嫁是相国护送的么?”王稽不经意随口一问。
“相国?客官是说苏珏么?他早就被罢黜啦,连封地都收回来了。”客栈老板娘小心翼翼地凑过来,压低了声音说道:“那告示张贴了好几日呢。”
“什么?”王稽“啪”地拍桌站了起来,他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客栈老板娘。
老板娘被他这举动下了一跳,拉了拉他的衣袖,凑近说道:“小声些,我王明令禁止市民谈论关于相国的一切事情。”
王稽掐了掐眉心,他缓了缓低声问:“店家可知苏公子如今在何处么?”
“不清楚。”老板娘摇了摇头。
王稽深深地皱着眉,内心翻涌的不安让他不敢在停留,即刻启程返回了熙国。
梅灏听罢,压抑地呼出一口气,苏珏还是楚相时所作的每一件事情都给中原诸国带来了莫大的震撼,那位眉眼温雅的相国总能很好地控制住局面,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消失的半点踪迹都找不到?
苏珏的消失让梅子玉产生了莫大的危机感,他抬头看向窗外,喃喃:“苏珏、楚云祁,你们想要做什么呢?”
王稽擦了擦额头的冷汗,他心有余悸地吞了吞唾沫,问道:“我们要做什么?”
“举国进行二次变法,唯有国强才可立于不败之地。我即刻便去面见我王。”梅灏冷静下来,顿了顿道。
倾国曲阳北城外校场。
景明身着玄铁盔甲,带着红缨头盔向倾王抱拳行礼,道:“北境一日不安,臣便一日不归。我王请放心,臣为倾万死不辞!”
倾王搂着一个美人慵懒地坐在惠瑜为他准备的毛毡上,头也不抬地点了点头道:“寡人于曲阳待将军得胜归来。”
沉重肃穆的鼓声一下一下敲在景明的心上,也敲在了校场上站着的五万将士的心上,此去经年,应是戈壁大雁相伴,胡笳羌笛入眠,执伊人之手,道一声珍重。
景明再次向倾王行了一礼,干净利落地转身,翻身上马,拔剑指天道:“出征!”
鼓声渐渐急促起来,五万将士整齐划一地拿起盾甲,“嗨”地一声,转身背对着曲阳城一步一步走向北方。
凤清将身子探出马车外,对骑在马上的景明道:“我想骑马。”
景明皱了皱眉,他道:“路途遥远,先生骑马是吃不消的。”
“啧”凤清挑了挑眉,扫了他一眼,道:“你怎地和个老妈子似的。”
“我”景明骑在马上愣了愣,他这一生活得太过严肃沉重,整个人显得过于不苟言笑,他与人相处的方式总是带着一种莫名其妙的仪式感,所以军中上下敬他,却不亲近他。这还是第一次有人以这样一种潇洒任性的方式埋汰他,景明一时间不知该说什么回应凤清。
凤清被他这样子给逗笑了,他将手肘搭在马车侧边开着的小窗上,薄唇微勾,浅笑着微微抬头看向景明道:“我就要骑马。”
阳光正好洒在凤清白皙的脸庞,明亮的凤眸恍若沉着整片星辰般折射出涟漪般的碎光,长长的眼睫在眼睑下投映出浅浅的影子,凤清一截光洁的脖颈从朱红色华服中露出来,薄唇微启,眼波流转,顾盼神采。
景明呼吸一窒,盯着他不由得失了神,凤清将他微妙的表情尽收眼底,他“啧”了一声,笑骂了句“傻子”,便放下了马车窗子的帷帘。
大军行了一月之余终于抵达倾国最北部的狄城。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狄城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者孤零零地矗立在稀稀拉拉的草原上。
距离狄城东面五百里的地方横亘着一座大山,倾人称之为燕支山,戎狄部族称之为那宿山,山的东面是茫茫的大草原,也是戎狄人的主力所在地,山的西面是半草原半荒漠的大漠,倾人或是放牧或是种植一些一年熟的旱作庄稼。
那宿山像屏障一样阻挡了倾军攻伐戎狄主力的脚步,所以戎狄人都将它视为神明之山。
戎狄一族偷袭倾国的战术战略在几百年的冲突下已经形成了一套体系:在秋冬季,草木枯萎的季节,戎狄王便将主力暂时迁往那宿山的北部,再派遣戎狄士卒绕过那宿山从北部的戈壁滩一直南下向倾国北境攻来,烧杀抢夺了足够多的粮食的牛羊后,他们又浩浩荡荡地退回黄沙漫天的戈壁滩。
倾国士卒都生活在中原地区,他们对戈壁滩这个吃人的怪物束手无策,曾经有倾君下令戍边将士强入北部戈壁滩,最终都有去无返,所以,这几百年来,倾人虽知戎狄对战策略,却没有半点应对之力。
景明换了玄色厚重的华服,神色凝重地站在城墙的箭楼上看着北边绵延不绝的草原,安插在戎狄部族内的斥候来报,戎狄王得知犀首率倾军前来北境后便召集各个部族的首领商议对策,听各部族首领的意思是要与景明来一次正面的交锋。
景明担心的正是这个,一直以来,他所面对的敌人都是中原各国士卒,是和他们有着一样文明的中原人,对于戎狄人,景明所知甚少,令他震惊的是戎狄人得知消息的迅速程度不亚于中原任何一个强国,以及他们的反应速度也是惊人。景明本想先在狄城按兵不动,等摸透了戎狄人的脾性在出兵,未曾想,戎狄人嗜战如痴,迫不及待地想和自己较量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