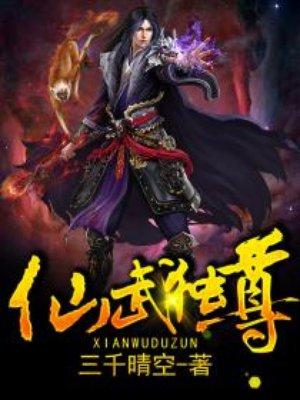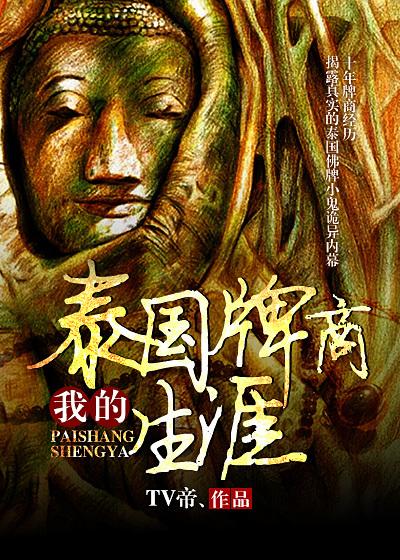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江南什么歌来着 > 第38章(第1页)
第38章(第1页)
此事原本便是冲着她来的,如今更多人的怨气却都冲着孟粤樟去了:“老师,抱歉。”
孟粤樟当然不可能怪她,但她提起这件事情,一直隐忍不问的苏朝哲便忍不住了:“苏苏,究竟怎么回事儿?”
看着满屋的人都朝她瞧来,苏媚叹了口气。
事情原也不复杂,但也称不上简单,期间牵扯到了不少人,也涉及到了一些旧事,苏媚并不愿在唐鹤逢的面前谈起,她抬头看了他一眼。
不知是在何处来的默契,四处相对之间他极快的转过了视线,冲着在场的几位长辈道:“此事便交给我,几位长辈不必为此忧心。”
说也奇怪,他明明不过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与他们这一群活了五六十年的人比起来应是青涩的,但他只简简单单一句话,便能令人格外信服。
势在必得,成竹在胸,他们能在他身上看到一种智珠在握的自信。
这种自信即便是如他们般活了大半辈子也难以修炼出来的。
但唐铭与他相处多年,并不好糊弄,他追问:“你要如何应对?”
“小叔,利是烧身火,搞不好是要玩火自焚的。”他语焉不详,其余人再问他也不再多说。
可怜满屋文化人一时之间在他面前竟都显得脑子有些不怎么好用。
苏媚隐隐约约的有些眉目,但却一直无法抓住,直到吃完饭,唐鹤逢送她会鹤卿小筑时她才开口询问:“你究竟打的是什么主意?”
闻得此问,唐鹤逢嘴角翘起一抹颇为高深莫测的弧度,他缓缓的吐出:“假之以便,唆之使前,断其援应,陷之死地。”
这是一招诱敌深入。
但紧接着他又说:“类以诱之,击蒙也。”
这是一招抛砖引玉。
但苏媚仍旧不解,唐鹤逢继续道:“重要的并非是我如何应对,打的什么主意,而是如果我想自然有无数办法解决,他们不过是跳梁小丑,不值得你费神。”
他的语气冷硬,说出的话也格外的乖戾。
至少这不该是那个面对沈培也能说出你很好的唐鹤逢能够说出的话。
苏媚盯着他的脸,看到他脸颊的肌肉轻轻跳动,她忽然福如心至:“唐深,你是不是有些不高兴?”
“嗯。”唐鹤逢并没有否定,显得无比的坦诚。
为什么呢?按照这个对话的发展,苏媚是应该问出这句话的,但不知为何,她有一种隐隐约约的直觉让她并未选择继续问下去。
苏朝哲询问时苏媚的欲言又止让唐鹤逢想起了一些并不好的回忆。
那是已经尘封很多年很多年的记忆,但即便是岁月不断揉捏,那些淬血的记忆仍旧鲜明。
他像是有些魇住了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