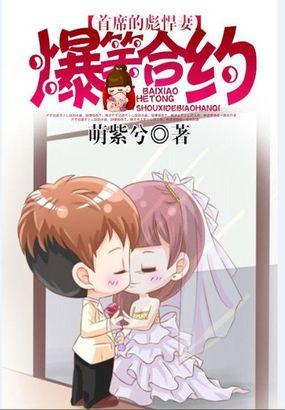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小女子这厢有礼了怎么回话 > 第99章(第1页)
第99章(第1页)
贺云初冷冷道:&ldo;你等虽是临时受命听令于我,却从未拿我做过主将,如今犯了律令却要我来惩戒,实在是高抬我了,我受之不起。既然你们有各自的听令之人,自己觉得哪里错里,但请前往请罪便是,我也只是虎假虎威充充脸面而已,当不得真也作不了数,如何行事大家自便。&rdo;
贺云初说完,也不再看他们脸色,转身就走。
陈陈站在后面,贺云初的每一句话都象一记重锤,声声都是给他的敲打。此刻他才发觉,其实真正错的人是他。他一直以为这位少尊主只不过是仗着在族中的身份和西北军两位封疆大吏不清不楚的裙带关系,是个恃宠而骄百无一用的傀儡。此番话却生生将他敲醒:掌政使能将阖族存亡重任交付与之的人,又怎会是泛泛之辈。
&ldo;是属下僭越了,最应惩戒的人应当是我。请各位兄弟代为行刑,不管何种刑罚,属下甘心认领。&rdo;陈阵倏地跪下,周围的人俱是一怔。
贺云初缓缓转身,伸手虚扶了他一把:&ldo;陈护卫是族中的老人了,族中的规矩自是清楚的,就算有错,也不是任谁想惩便能惩的,您是我等的前辈,领兵经验富足,这一路上众位兄弟还要靠您提点知悟,除非您是想就此卸了身上这付担子去了,否则,休要再提惩戒之事。&rdo;
贺云初此番明捧暗戒的话,可谓心思缜密,陈阵在掌政使身边多年,要再听不出她话中的机锋,便枉费他被拘禁这数年所受的折磨了。
午后阳光的炽热渐渐升起,好在有一丝送爽的微风,伴着阳光的亲抚徐徐吹过,官道,竟没有之前在戈壁滩时那般的酷热难耐了。西北道的四月天,气温还是凉的,道路两侧,也只有向阳的一面嫩绿的小草才刚刚在风中舞蹈,阴面还是光秃秃的一片。冷热交替下,使得负重远行的人马即不用担心酷热难行,也不用担心寒意彻骨,行得倒是轻松舒坦。
渐渐的,空气中伴着尘土的味道而渐来渐浓的血腥味,让所有人都不那么舒服了。东北方向,远远的甚至可以看到天空中盘旋的乌鸦和秃鹫,如压顶的乌云般,摭蔽了半边天空。
☆、良程诡迹(一)
贺云初下令队伍停止前进,陈阵指挥人马将所有的马车和贺云初一起护卫到中间,全队拉出迎战的阵型。
贺云初朝身后打出个手势,队伍中,立刻跃出五骑,朝着东北方向而去。乌鸦和秃鹫出现的地方,必是因血腥之气,而如此数量庞大的乌鸦和秃鹫出现,血尸的数量想必也不会少。
轻伤的斥侯现在已恢复到能单独骑行,有了斥侯的队伍,行动也不再盲目。
但随后斥侯报回的消息却令贺云初大为惊诧:&ldo;在下三河段,一百多具尸体丢在那儿,从他们的服饰来看,象是定州军。&rdo;
贺云初盯着天上依旧在盘旋的黑色阵营:&ldo;若让尸骨的味道引来鹫群,暴尸体之气至少要在烈日下熏蒸数十个时辰。数十个时辰前,应是昨晚至昏未黑之时,如果是大队人马厮杀,必有可寻之迹,再探。&rdo;
如果血尸真的是定州军,百十来人的定州军深入西北道腹地夏州,必不是身负重任之师。那么又有谁会对一支毫无威胁力的人马下此狠手?
外出的斥侯回来了,被陈阵拦在外面似乎在询问。远远的看到贺云初,斥侯一侧身躲开陈阵,朝着贺云初奔过来。在西大营,他们只听贺云初的吩咐,任是许峥或是贺靖,都别想从他们嘴里知道想要的消息。
斥侯年龄还有些小,显然是刚入军不久的新兵,看到主将后难掩脸上的兴奋之色:&ldo;昨晚有当地人看到过这里的厮杀,好像是一帮伤残的土匪所为,偷袭了在这里歇息的这支人马。&rdo;
&ldo;土匪?&rdo;贺云初简直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ldo;可知是哪里的土匪?&rdo;
&ldo;不知道,不过从他们描述的情形来看,与昨日冲闯柳原镇的那支应该是同一支人马。&rdo;
也就是说,那也是一支伪装成匪的军中劲旅!可又是哪一支军呢?&ldo;可是探得那支人马得手之后去往了何处?&rdo;
小斥侯摇了摇头:&ldo;战后起了黑风,风止之后那些人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rdo;
陈阵深邃的眸子盯着天空的鹫群望了半天,象是自言自语,又象是故意说给贺云初听的:&ldo;昨日隆裕行的护卫跟沙匪伙拼,侥幸逃出了两个。&rdo;
贺云初一顿:&ldo;这么大的事,怎么……人呢?可知在何处?&rdo;
阵陈也不介意贺云初的微怒,侧身朝贺云初点了点头:&ldo;你随我来。&rdo;
队伍中间,被十几匹马夹道而行的果然有两骑上驮着捆得象麻袋一样的两个人。
十几骑打马围了一个圈,中间的一处空地,两个捆得象麻袋一样的人被扔在中间。由于天热又是一路的飞尘,汗水和尘土把他们的脸糊得几乎看不出了原本的肤色。兵士抓住其中一个俘虏的头发将他拎起来:&ldo;大人小心些,这东西厉害的很,伤了我们十几个弟兄,要不是陈大人撒了网,根本捕不住他。&rdo;说着,在他背上狠击了一拳。
这是一张窄小的似乎没有长开的脸,即使被尘泥糊得看不出原本的肤色,却也能认出他还是个孩子。他的四肢都被捆束着,被强迫直立起来时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满是戒备地瞪视着贺云初,竟未见一丝惊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