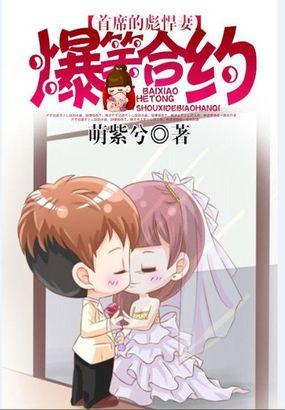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浮光fm官网 > 第4章(第1页)
第4章(第1页)
潘霏霏立刻垮下脸来:「没觉得……我都在看言采,哪里有时间关心别的。」
「你这哪里是看戏……」
「看戏的法子多了。你这样是看,我就不是看了?」
她说得振振有词,完全没有留心身边那个自开演就空著的座位忽然坐下一个人来。谢明朗倒是比她先留意到了,瞄了一眼,昏暗的灯光下只能看见是个年轻男人,一落座就勾下头,不知在想什麽。
谢明朗就笑著说:「好好好,是看,是看。粉丝看人,我看戏,这还不行吗?不过我事先对这个戏一点都不瞭解,现在还有些地方没弄明白……」
「什麽?要不要告诉你?为了这齣戏我可是仔细做过功课的。」霏霏眼看著又来了精神。
「看你念书没有这麽上心过。」
「喂喂,这个时候就不要摆出一副大哥的架势来教训我了。明明是你说你有不清楚的地方。」
「我就是随口一说,也许下半场就明白了。」
「你怎麽知道不是越来越糊涂?」
「霏霏,你今天太兴奋了。」
「有吗?」潘霏霏一笑,「那就是吧。」
果然到了下半场,上半场一些让谢明朗不解的地方渐渐明朗:他终于明白莫利纳的阴柔从何而来,也明白了两个人相处之时古怪的张力和莫名的距离感。
戏剧走向尾梢,瓦伦蒂选择回应莫利纳,那一刻灯光全暗,一切都成了暧昧模糊的剪影,挤在一张单人床上的两个人虽然没有直接明瞭的举动,但其间的性暗示,已经足以让观众明白接下来应该发生是会是什麽。
谢明朗第一个反应是去看潘霏霏,黑灯瞎火的,几乎什麽都看不见,不过令他惊讶的是,霏霏并没有像他以为的那样目不转睛地盯著舞台,而是时不时飞快地往她另一边那个座位上的人转过头,显然是在偷偷打量对方。
但他来不及深想,灯光谢天谢地地亮了,他就著看潘霏霏的姿势也瞄了一眼那个中场时才落座的年轻男人,在收回目光的那一瞬,瞥见一张异常英俊的侧脸。
谢明朗不好多看,重新把注意力收回到舞台上,这一夜之后的两个人相处时难免尴尬,却又多出了之前没有的温情脉脉。故事还在进行,谜团慢慢解开,年轻的革命者依然是个囚徒,被当作棋子的同性恋者却被幕后那看不见的当权者下出另外一步,假释。
最后那一个故事还没有说到结局,两个人就要分开,告别前彼此忽然想到他们做过了情人间一切应该做的事情,唯独没有亲吻。
于是他们用力拥抱,瑟瑟发抖,然后热吻。
从谢明朗的位置上能够看清楚舞台上两个人亲吻时的神态。作为表演,这个舌吻过于逼真了,对于谢明朗而言,简直到了令他不安的地步。他看见郑晓专注而投入的神情,也看见言采最初微微的畏惧,和稍后那让他不解的近于无动于衷的冷漠。
他莫名尴尬,不是因为男人与男人之间的舌吻,倒更像是忽然闯进某种亲暱私密的气氛,因而使得他更加坐立难安。
故事是这样结尾的:
莫利纳的死讯以画外音的方式给出,同时瓦伦蒂一脸痛苦地在床上挣扎。四周的背景都暗下去,只有他躺著的这张床给了灯光,他身边是医生,说,他们在折磨你。我给你一针吗啡,你就能忘记这些折磨,好好地睡一觉了。
所有的灯光再次熄灭,瓦伦蒂的声音同时响起,平静而安详,飘忽得彷彿梦境一般。
那也的确是幻觉了。
他眼前浮现起女友的容颜,她似乎在看著他,与他交谈,带给他勇气与力量。他就告诉她蜘蛛女的故事,她蒙著银色的面罩,蛛网成了身体的一部分,她在哭泣。
最后他听见女友说了句什麽,无意识地重複出来,这梦虽然短,却是幸福的。
一切归于黑暗沉寂。
几秒锺彻底的沉默之后,零星的掌声响起,很快掌声彙成一片,其中夹杂著女人激动的欢呼声,很快整个剧院灯光全亮,先一步离开舞台的言采不知何时回到台上,和郑晓两个人一起向观众谢幕。他们一脸都是汗,明亮的灯光下,额头一块亮晶晶的;无数细小的灰尘纷纷扬扬聚向他们,好像某种不知名的魔法。
很多人站了起来,想看得更清楚一些。谢幕时候的言采又变成了大家都熟悉的那个,阴柔的女子气一扫而空,乾脆地朝各个方向的观众鞠躬致谢,直起腰来的时候,笑容中的朝气,让整个人一下子灿烂起来。
潘霏霏一边死命拍掌一边抹眼泪,谢明朗不时朝她看一眼,想问她是因为见到言采太激动,还是真的被戏剧本身感动了。这样的动作让他又不免看到隔了个座位的那个年轻男人,也在用力的鼓掌,目光同样专注热切。
言采和郑晓返场一次之后,不管观众是多麽热切地鼓掌想再见他们一次,还是没有再出现在舞台上。年纪大的观众已经陆续散了,仍然疯狂地鼓掌欢呼的大多是言采的影迷们。潘霏霏也不肯走,最后索性也站起来,踮起脚往后台的方向死命张望。
谢明朗叹了口气,拉著她说:「他一週演六天,要是每次谢幕谢个七八回,那就累死了。好了,我们走吧,我请你吃饭。」
潘霏霏还是不死心,谢明朗几乎是用拽的了:「你再这样,下次还有票我怎麽敢带你来?你妈知道了,又要说我带坏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