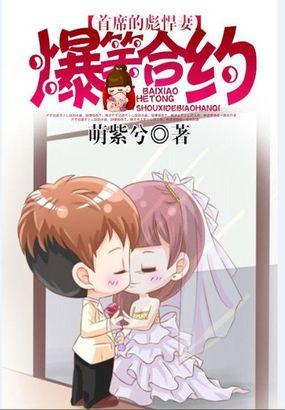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云烟旧事by > 第75章(第2页)
第75章(第2页)
看来是真的。
屋子窄而暗,但一进去,扑面来都是她身上独有的气息——一股淡淡的粉香,与许多年前一样的,没有变。
阿桢点了灯,带着笑轻轻说,“多谢你,把安安带回来。”
他回,“不用谢。”一边看了屋里的陈设——也并没什么陈设,不过是些底层百姓家最基本的家常物甚,一些看头也没有。
关了门,没了太阳,又是莫名的冷。
她搓着手,说了声,“西北朝向的屋子,当初看便宜才租下来的,有些冷。”就过去生火盆,间隙,又閒散地问,“你过得还好吗?”
小暑答了声,“还好。”觉得声音都不像是自己发出来的。
她专心致志,很快便生好了火盆,又笑,却也不说别的话。
他也是沉默。
一时里,空气又像凝固住了。
他点了支烟抽起来,发觉她看着他,他也回看她,很自然地问她,“你要么?”
阿桢一怔,脸上却仍带着笑,“我早戒了。你倒好,几年里,什么坏习惯都养成了。”
小暑自顾自地吸烟,并不去否认,“人总要变的。”
她又是一怔,有些黯然地垂下眼去,“是啊。总要变的。”
他一支烟吸完,碾了烟头,又不声响地坐着。
黄昏的暖光透了窗,温和地洒进屋里。
正是烧夜饭的时候,别家在炒菜,各式各样菜的油气混了一道,复杂地升腾起来。
阿桢站起身,温和地问,“饭吃了么?在我这随便吃点?”
他并没应允,却也没反对。
她真的就去做饭,打开碗橱拿了些东西,对他说了声,“你等一会儿,就好的。”就到门口去。
煤球炉的烟气透了门缝飘进屋里,只听见“刺啦”一声,又是什么东西进了油锅,随后是锅铲的碰撞声。
他仍坐着没动。
阿桢端了两碗炒饭回来,搁在桌上,又从碗橱里拿了两双筷子,笑着招呼他,“好了。来吃吧。”
他终于起了身,和她一道坐到了桌子前。
是碗蛋炒饭。
她慢慢地吃。
小暑吃了两口,就再咽不下去,搁了筷子不动了。
他看见,她的手指边缘生了层薄茧茧,年纪上去了,脸上也不再如过去一样细嫩无瑕,不可避免地生了一些细小的纹路,大概是真吃了不少的苦。
阿桢抬起脸,“不好吃?”
小暑不答,她嘆气,又笑笑,“对不住,我做东西就这些水准。”
他直直地看她,她也回望他,忽然看见了他藏匿在额发里的那道疤。
她不由自主地伸了手过去,轻轻撩开他的头髮,手指尖触到那疤时,他皱了眉,本能地朝后退了一下。
肌肤相触时,有一种颤栗从那相连的部分升腾起来,一直蔓延到了骨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