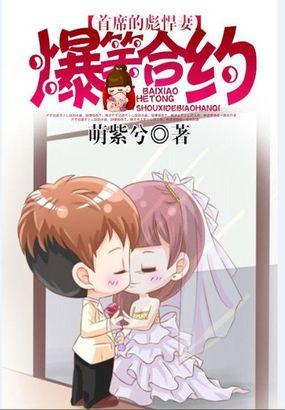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乔画凤昭战神凤枭 > 第71章(第1页)
第71章(第1页)
那件事,因为秦洛和他父亲的缘故,先帝只当是俩孩子不懂事,打趣几句、各赏了些金银珠宝了事。
在他那儿,事情就没完了。
之后的日子,只要得空,只要有机会,就会到宫里或者她当时的住处找她。
起初每次都被她挖苦,都要受她的冷眼。不好受。那也得去,不然更不好受。
终于是守得云开,终于是她肯给他好脸儿了,跟他熟稔再一点点亲近起来。
真性情的令言,特别可爱的。
真的。反正在他这儿,这辈子都没见过比她更可爱更招人喜欢的女孩子。
谁都不知道,他有多爱多心疼她。
连她都不知道。
不,是她最没心肝最冷血,不肯知道不肯在意罢了。
那么久之前,她问他:“你所谓的喜欢,能有多喜欢?”
他想了一会儿,说:“我也说不准,估摸着是出乎你我的预料、想象。”
——那句话,偶尔会让他觉得,是他对自己此生埋下的一个诅咒。
最恶毒最让人没法儿承受的诅咒。
那份感情给过他最美的狂喜,也给过他刻骨铭心的痛苦。
喜悦时少,痛苦时多。
他都得收着、受着。
几年了,一日一日,一颗心总在炼狱中挣扎。
爱不得,放不下,一直有一团烈火焚烧着吞噬着心魂。
都到这地步了,都煎熬得快疯了,还是喜欢着,爱着,等着。
这是有多贱啊?——郗骁这样挖苦着自己,侧头看了沈令言一眼。
她神色沉静冷漠,像只无辜孤傲又孤独的猫。
郗骁背在身后的手动了动,想掐住她的脖子锁住她的咽喉,想让她因为窒息而失态示弱。
只要她不再无动于衷。
只想撕破她那张不死不活的面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