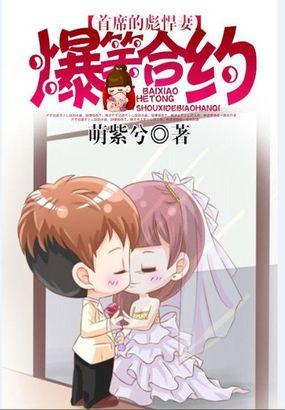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金光布袋戏默苍离 > 第23页(第1页)
第23页(第1页)
“他可是堂堂的妖界之主——西苗王啊。”
“他怎么可能只是一只好心好意,单纯为了陪伴你而留在你身边二十余年的……普通狼妖呢?”
那只手在即将碰触到俏如来时却停下了动作。俏如来慢慢偏过头,在视线昏蒙间似是看到有一人护在自己身前,身形高大,巍峨如山,让他觉得熟悉却又陌生、亲近却又疏离。
他见那人紧紧捉住竞日孤鸣伸向自己的手,侧颜朦胧,不可明辨。那人身穿的玄紫衣袍华丽繁复,妖气震荡间将宽袖披风一道带起、上下纷飞。俏如来只觉身上重压骤然变沉,意识也愈发昏沉,仿佛就要散去,然他在这一片朦胧中却见得眼前人双眸明灿,深如幽潭,色若瀚海,亦是无比熟悉。
那人眼光如刀,直直盯着竞日孤鸣此刻似笑非笑的脸,薄唇微启,嗓音低沉磁醇,落入俏如来耳里,熟悉地让他心生怆然:
“祖王叔……竞日孤鸣,你,踩过孤王的底线了——”
一言语毕,重压陡增。妖界双王的磅礴妖气在空中互相对抗冲击,带起余波阵阵,久不能散。俏如来被这突入而来的激烈对抗压得窒息,双膝跪地,汗湿肩背,大口重喘,却无法换来胸中半分纾然。他似是支撑到了限界,眼前景物已然全黑一片,身子发虚,四肢发软,在下一波妖气碰撞时彻底失了气力,软倒在地。
在彻底晕去前,俏如来似是看到一双熟稔无比的蓝色双眼。他下意识地伸出手,想要碰触眼前的那双暗含愧疚与关切担忧的眼,然在意识消散前他所能抓住的,只有一片空泛无边的虚无。
※
俏如来醒来,已经是五天之后的事了。
在这五天里,战局突变。妖界西苗辅政亲王千雪孤鸣与魔界幽暗联盟大将西经无缺率大军赶到,以“除缴妖界叛逆”之名杀入战圈,助鳞族军队与联军对抗。妖、魔二界联军虽在与鳞族对战中占尽优势,但仍不敌西苗与幽暗联盟联军军势,受到重创,尽数败逃。应龙师在与西经无缺对战中身受重伤,领凶岳疆朝部众退回魔界;东苗王竞日孤鸣则在混战中失去行踪,其所领东苗残部四下溃散,尽数为西苗所虏,“东苗”一国,名存实亡。
鳞族众人皆对千雪孤鸣与西经无缺感恩戴德,都说是因二人率军及时赶到,抢先重创联军将领,挽救了几成颓势的战局,才让人界与鳞族能够逃过一劫。
然俏如来心知,鳞族众人所言并非全是真,重创应龙师之人是谁他并不知晓,但逼退东苗王竞日孤鸣的不应是西苗亲王,而是……
西苗王,苍越孤鸣。
他正想着,便听到帐门帘布被撩起而发出的扑簌声。俏如来回过头,首先对上的便是一双再熟悉不过的眼,他看着苍越孤鸣走到自己身前,犹豫片刻,终是没有如往常一般亲昵地凑至自己身旁。苍越孤鸣在离床一尺的地方端正坐下,尾巴搭在一旁,双耳微垂,眼光半错,不言不语。
俏如来坐在床沿,双手捻着掌中那串白晶念珠,双眼带着些探寻的意味望着苍越孤鸣错在一旁的眼,半晌没有说话。他想从那双眼里读出些什么,哪怕是只言片语也好,但他在那两汪幽蓝中没有读出任何东西,哪怕是分毫能让他稍作释怀的情绪波动也无,平平静静,宛若死水。
他这番情状,是谎言被破后的破罐破摔?还是底牌尽露后的异常冷静?俏如来不知,亦不想知。苍越孤鸣的平静无言让他心焦,不予辩解也让他失望。俏如来只觉往日的相依相伴皆是一场荒诞异常的笑话,自己将他视作至亲真心以待,换来的只是这二十余年的欺瞒与谎言。
他为何隐瞒身份?他为何不实言相告?俏如来心如刀绞,太多的想不明与道不清纠缠一处,让他如嚼了口黄连在嘴里,口与心皆是苦涩难言。
掌中晶珠坚硬硌手,怀中菩提热烫熨身,俏如来却无力顾及。他在身与心的煎熬中做下决定,十指扣紧,双眸微抬,开口言道:“西苗王何必屈尊纡贵维持兽形?不如恢复人身,方来得自在。”
本是清亮朗润的声音此刻干涩一片,平稳无波,不带一丝情绪。俏如来将双手松开,交叠放再腿上,那晶石的珠子就绕在手间,用力攥握的动作让那念珠深陷皮肉里,硌得掌心都是一片生疼。但他对此却毫不在意,浑然不觉痛楚似的将手攥得更紧,眼却忽地垂下,凝视着掌间晶莹剔透的佛珠,缓了一会儿,才继续说:“俏如来先前不知西苗王身份,行为逾矩,多有僭越,还请西苗王宽恕。俏如来日后定会注意身份,不会再行逾矩之举。”
他口吻谦然,一口一个“西苗王”,一口一个“俏如来”,一句一句皆装作卑微谦下,像是低微到尘埃里。他虽这般说着,眉目神情却仍是平缓无波,一双绯色的睫半颤微垂,遮住望向苍越孤鸣的视线,也掩住了那双光华逐黯的眼。他似是要用谦卑疏离之语筑起一堵无法逾越的高墙,将人族与妖族、平民与君王、俏如来与苍越孤鸣彻底隔绝拉远,从此江湖高远,再无牵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