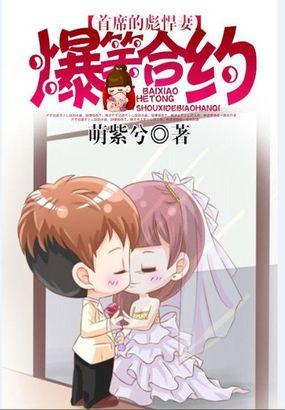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如果我能告诉你常闲书包网 > 第21章(第1页)
第21章(第1页)
&ldo;没关系的,&rdo;连湘快活的说,&ldo;只要你收留我就好了。我们学校宿舍的条件也没有多好,还一堆人住呢,你放心,我没那么娇气的。小谧姐,你以前在国外时,住的是什么样的地方呢?我听说国外的学校并不提供宿舍,我哥就是自己租的公寓。&rdo;
&ldo;嗯,是这样。我也是租公寓住,有的很好,有的很破。&rdo;
&ldo;好的什么样儿?破的什么样儿?&rdo;
&ldo;好的和我原来在宁城住的那个差不多,有那个三分之二大吧,当然没那么精致,窗户也小些,也没那么新。差的嘛,你想想你见过的最破的住宅楼,咱们路上就经过了一个,应该是建国初期建的。他们欧洲因为房子都是私产,也不能强拆,四处有的是那种很老的房子,上下水都不行,电路也不好,我就住在那里。&rdo;
&ldo;啊?那你为什么会从好的搬到差的去了?&rdo;
柳谧笑,&ldo;你这就和那个说&lso;何不食肉糜&rso;的晋惠帝一样,当然是因为没有钱啊。&rdo;
她起初当然不是住在这样的公寓里的。虽然欧元比人民币的汇率很高,但以她家当时的境况,当然支付得起。公寓虽然不大,但离学校近,舒适安全。她从小就对钱没什么概念,银行卡里永远有足够支付的钱,米尧还特地给她建立了个需要支付的大额账单的备忘录,时不时的登上她的账户看看情况,以至于在她家出事后,她都忘了取消有些并非是生活必须的习惯性消费,也自然忘了取消需要定期预付的账单。这让她的财政情况雪上加霜,等她回过神来的时候,已经是有大把的账单因为没有付而收到特别提醒了。
从天堂到地狱,总是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她搬离了高级公寓,一开始还不能接受太破的公寓,后面就越来越习惯,也越搬越破、越搬越远了。
连湘忽然问了一句,&ldo;那你那时不认识我哥?&rdo;
柳谧一时没回过来神,&ldo;认识,怎么了?&rdo;
连湘的声音里带着指责,&ldo;他怎么不借钱给你?&rdo;
柳谧的声音低了下来,&ldo;是我自己不想要。&rdo;
&ldo;为什么?&rdo;
&ldo;还也还不上,就不要借了。&rdo;
那时连浙对她生活的干涉很多。他曾给她找了间房子,强迫她搬过去;也曾替她交了学费,想让她继续学业;还曾经去举报那容留她□□工的店,让她不能再去那里。他不断的替她作主,她就不断的反抗。现在想,如果不是连浙,那个时候她真的随时都有可能离开这个世界。
一直到连平域找到她。一切戛然而止。
&ldo;那你和我哥是怎么认识的呢?&rdo;
&ldo;其实……我也真不大记得了。好像是在一个露天的party上,但我没什么印象了。&rdo;
&ldo;那又是怎么熟悉起来的呢?&rdo;
柳谧笑,&ldo;你真八卦。&rdo;
&ldo;哎呀我学习一下嘛。&rdo;
要说和连浙怎么熟悉起来的,好像也只有是音乐会。
听音乐会是从小养成的习惯。因为从小就立志要学艺术,只要来安城的音乐会,她都会去看。大了点儿之后,米尧还陪她去过外地听演奏会。到了欧洲后,顶级乐团就在身边,各类音乐会次第开会。反正家里也负担的起,她也没有别的爱好,米尧也还在国内读书,大把的业余时间,她基本就在各种音乐会中度过。
一次她去听一场小型的吉他音乐会,散场的时候,她不喜欢和人争抢,一般都是最后走,在满剧场将暗的灯光下,居然看见连浙,她有些讶异。他则面带微笑,&ldo;好巧,又碰上了。&rdo;
实话说,她那时并不讨厌连浙,衣帽整洁,彬彬有礼,话不多,也会经常和她请教音乐知识。她发现他不懂,但品位不错,也非常有自己的个性。他不喜欢肖邦,她曾打趣他应该不是个喜欢浪漫的人。他倒慨然承认了,&ldo;即便是最浪漫的爱情,在我的眼里,也绝不是花前月下。&rdo;
她好奇,&ldo;那是什么?&rdo;
他看着她,眼光灼灼,&ldo;我希望能承载她的一切,也裹挟她的一切。我的就是我的。一旦开始,便没有结束。&rdo;
柳谧听得咂舌,&ldo;我怎么嗅到一种小白兔落入大灰狼的感觉?&rdo;
他一笑,&ldo;那就希望那只小白兔不要落进来吧,免得被我吃了。&rdo;他补充了一句,&ldo;没有逃得可能。&rdo;
当时只道是笑谈。她也没放在心上。一年以后,她家出事,她在世上霎时只剩下孤零零的一个,突然其来的变更让她蒙了。她不知道还能相信谁。
父亲一生荣光,死的那么寂寥灰暗。都说是米尧父亲举报的,铁证如山,父亲即便活着,也难逃定罪的命运。她不知道怪谁,也不知道该找谁理论。债权人蜂拥而来,她父亲公司的法律顾问告诉她,公司资不低债,父亲为了公司融资,还对外做了好多担保。如果她要继承财产,那就得继续父亲的对外债务。她也没来得及多想,就放弃了继承。然后,像是潮水一样,家人、财产,瞬间被卷的什么也没有剩下。她已经没有什么固定的地方住,还有人不知从哪里弄来她的行踪,恐吓让她父债女还。
她害怕极了,匆匆的回了欧洲。候机的时候,她在机场大哭。觉得天地茫茫,不知道哪里不容得下自己。长了这么大,一直被捧在手心里,原来有多透明、多纯粹、被保护的有多经心,这次跌的就有多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