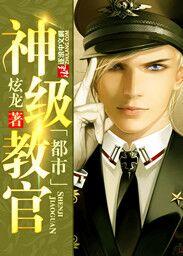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巧逞窈窕二番外结局 > 第170页(第1页)
第170页(第1页)
被戴庭望揭破,茂英脸色有些难看,索性说道:“豫章王贼心不死,不尽早斩草除根,怕后患无穷。”
戴庭望眉头微蹙,“豫章王已经是穷途末路,殿下何必赶尽杀绝?陛下亲政在外,朝政人心未稳,贸然行此举,弊大于利。”
连戴庭望也坚决不肯,茂英一时词穷,燥火在胸中翻滚不休,她走回侧殿,将帔子丢开,敞着雪白的脖颈,任清风自窗口吹拂在身上,偶一侧首,见戴庭望已经退到了殿外,十七八岁的宫婢一面用簪子逗引着金笼里的雀儿,一面害羞地对着他微笑。
茂英冷眼旁观,俄而一笑,对庭望柔声道:“正说着话,你跑那么远干什么?”
她突然放软的语气,令戴庭望有些不舒服。他垂眸道:“殿下的寝宫,臣还是站在外面回话吧。”
茂英摇曳生姿地走了出来,手往戴庭望臂膀上轻轻一拍,笑道:“论理,你该叫我一声母亲的,不必这么拘束。”不等戴庭望变色,她移开脚步,从宫婢手里接过簪子。宫婢垂头退了下去,茂英沾了些清水,点在雀儿尖尖的喙上,她幽幽一笑,说道:“你别站那么远,我真有话要问你的。”
戴庭望站在廊下没有动,只道:“殿下请说。”
茂英掠他一眼,说:“你小时候在陇右,时常看见秦氏伴随在陛下的左右吗?”
戴庭望踯躅着,点了点头。
茂英攥着金簪,望着笼中雀轻轻叹口气,说:“你叔父是个情种呢。”
这话戴庭望没法接,顿了顿,他皱眉道:“殿下没有别的事,臣先告退了。”
“别呀。”茂英放下金簪,人走到了戴庭望面前,她纤长的睫毛拢着眼底的哀愁,看着庭望微笑道:“陛下大概到现在心里还惦记着秦氏——我和他成婚几年了,他从来没有碰过我一下,你说我是可怜呢,还是可笑?你以后可千万不要像他一样啊。”
戴庭望愕然,有一阵才反应过来,脸色有些硬,“殿下要是为了姜绍和豫章王的事,臣是不认同,除非殿下有陇右来的圣旨,那臣也只能从命了。”茂英有些微凉的指尖落在他手背上,他立即甩开,有宫婢贸然闯入,撞个正着,吓得忙退避开了。
茂英看着他微红的脸扬声大笑,眸里闪烁着得意的光芒:“我要赐死豫章王,你非要作梗,以后宫里有什么难听的话传出来——我是不在意的,只不知道你那个叔父,还会不会把你当亲生儿子一样看了。”
“殿下自便吧。”戴庭望隐忍着怒气离去。
翌日乃是戴度虞祭,戴庭望以太子身份主持了祭礼,程氏携着女儿含泪施礼。礼毕,朝臣陆续退去,舍人周里敦将裱好的祭文送来给太子过目,戴庭望把卷轴放在案边,问道:“皇后跟你提过要将姜绍调离西川一事吗?”
周里敦道:“皇后昨日传了臣,命臣向陇右请旨,臣还没来得及动笔。”
戴庭望点头道:“你先按下此事,皇后问起,就说陇右军情繁忙,尚无回信。”
周里敦做了中书舍人,更体会到了朝政的风云诡谲。他审慎地观察了一眼戴庭望的表情——年轻人的城府颇深,并没有露出丝毫异色。周里敦垂首说:“臣知道了。”
戴度的遗孀程氏正在门口张望,待周里敦离去后,她走进来,犹带泪痕的脸上对戴庭望露出一点笑意。此刻没有外人,她才敢仔仔细细地打量了戴庭望几眼,拉着他的手道:“我在门口,依稀听了几句……皇后要打发姜绍,你顺着她就是了,何必违逆呢?”
戴庭望道:“母亲不懂这些,不要替我操心了。”
程氏黯然叹气。这个儿子已经不属于她了,她忧心忡忡,却无以言表。沉默了一会,忍不住低声道:“你毕竟不是嫡亲的皇子,这个太子做得名不正言不顺,你父亲又和陛下素有嫌隙……他们夫妻一体,到时候闹起来,难保陛下会偏哪一方。我听说陛下身边的姚嵩,和皇后交从甚密,你得提防着这些人啊。”
戴庭望对程氏安抚地一笑,说:“母亲放心,这点城府都没有,我们又何必从朔方来岭南?”
程氏又淌下来泪来,“你越这么说,我越不放心了。等明年除服,你就和县主合卺吧,有人陪着你,我也放心些,要是有了孩子,那就更好了。”
戴庭望脸上一红,说道:“这种事要陛下做主了,你我说了都不算的。”
回宫后,戴庭望着意安抚豫章王,屡次赠送厚仪,又将豫章王府守兵撤回大半,豫章王感念太子仁慈,提起许久的心也终究放了下来,被固崇怂恿着,亲自进宫谢恩,一对君臣,重修旧好。
此时的朔方,草长莺飞,神策军驻军灵武后,抢先收割了春麦,坚壁清野。温泌率军抵达平凉,见田垄上光秃秃的,一粒粮食都不剩下了,他双手叉腰,在地头来回踱了几圈,望着邻近村落袅袅的炊烟,对韩约悻悻然笑道:“晁延寿坐等我们来助他抵御戴申,却连一粒米都不舍得给咱们吃。这场仗要是靠他,恐怕你和我连裤子都要输给戴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