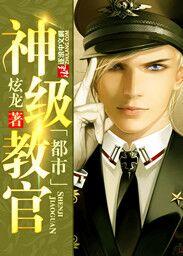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私自占有公共财产 > 第59页(第2页)
第59页(第2页)
“谁让他有钱嘛,”我安慰她,“要他一个人估计得坐飞机。”
“神经病,”乔若愚烦道,“非说不放心我,我去,我对别人不造成威胁就不错了……”
“你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送你?”
“为什么?”乔若愚警觉地问,随即鄙视道,“你还不知道吧,他说他想跟我去看看我们学校有没有美女,真烦死了。”
“乔儿,我是真不知道,你到底是大智若愚,还是大愚若智。”
“你怎么骂人呢……”乔若愚果断偏离重点。
最终乔若愚还是妥协,让夏眠跟着一块上了火车,临行前抱着我半天不肯撒手,我向她承诺国庆节一定去她学校里找她玩儿,她才依依不舍地松开了我。
乔若愚离开后,我沿着火车站漫无目的地逛了一下午,才回家收拾好东西,第二天去学校报道。
虽然在本市,从家里到学校打车还是得一个多小时,我独自拖着行李踏入相对比较熟悉但也全然陌生的校园,突然有一瞬间的茫然。
像不知道自己是来干嘛似的。
大学生活不似高中,不比以前那样紧迫又处处压力,但每天总有各种乱七八糟的事不得不做。我强迫自己心无杂念投入这种轻松却令人烦躁的生活里,试着尝试一件件感兴趣的事,接触形形色色的人,慢慢融入这种环境。
再后来,开始认识了一些班级以外的人,会与别人建立起各种关系,疲倦也无妨,也有碰到很有趣的人,但总提不起兴趣,我好像活在人群之中,又好像游离在自己的世界以外。
重新开始一段关系很容易,我却一点也不想再经历那些过程。期待着什么但又时刻死心的感觉让我快要忘记一段感情最初的简单是什么滋味。
割舍一段关系,比重头开始更需要勇气。
好像从何景之以后,我对别人的好感,开始连多看一眼的心思都不再有。
国庆节我没能去找乔若愚玩,因为她回来了一趟,说想爷爷奶奶了。我只好把承诺往后推迟,挪到元旦。
全身心投入一段生活时,日子就仿佛过的特别快。
转眼又是每年的最后一天。
我买好车票正打算出门,有电话叫我去楼下取一下包裹。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思来想去也没记起这段时间网购了什么。
电话一直摧,我只好先去楼下快递站拿包裹,是一个小箱子,我不禁纳闷,于是当场拆开来看。
是一个篮球。
和那个被我当成生日礼物送出去,又被我收回来亲手毁掉的礼物,一模一样。
我抱着箱子在快递站愣了很久很久,浑身僵硬,快递员在我身旁担心地问,同学,同学,你没事吧。